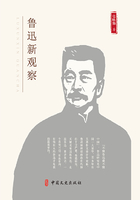
第2章 出售“鲁迅藏书风波”始末
1.从朱安说起
在鲁迅的生活中,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尽管他们名为夫妻,却名存实亡,形同路人。这个人就是鲁迅的夫人朱安。
三四十年前,开始接触鲁迅作品的时候,我只知道他的爱人是许广平,鲁迅那句著名的诗句:“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就是他们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朱安的名字却始终被遮蔽、被隐藏,她和鲁迅的夫妻关系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生前死后始终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鲁迅为什么不接受妻子朱安?许多人出于维护鲁迅的角度,都说是因为朱安没文化、裹小脚,两个人志趣相异,没有共同语言等等。这些说法都可以理解,也是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的原因之一,但未必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朱安不够漂亮,缺乏女人的魅力。
鲁迅的婚姻是失败的,在他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既然母亲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一厢情愿地喜欢她自己选中的儿媳,那鲁迅也只好将这个“礼物”完好无损地还给母亲。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鲁迅终其一生也不接受,更谈不上喜欢。朱安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爱情,孤苦凄凉地走完悲惨的一生。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转年十月与许广平共同生活于上海。朱安与婆母鲁瑞生活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寓所,靠鲁迅每月寄钱赡养。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朱安没有继承丈夫在上海的遗产和版权,全部交给许广平全权处理,得到的承诺是:生养死葬,安度晚年。随着物价上涨——米、煤、蔬菜均较以前上涨了两三倍,鲁迅生前每个月提供的一百元生活费不敷使用,他的母亲鲁瑞希望许广平增加家用的要求得不到回应。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周作人开始负担母亲的生活费,每月五十元。朱安仍由许广平每月筹寄四五十元左右,虽然标准略低,但大致维持鲁迅生前的数额,生活水平无疑有所下降。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监狱七十六天,出狱后因自身困难和邮寄不便等原因,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断了对朱安的生活供给达两年多时间,并一度与北京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开始负起赡养母亲和寡嫂朱安的部分责任。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迅的母亲逝世,临终前将周作人每月给自己的十五元零用钱转给朱安。这十五元大洋折合当时的“联准票”一百五十元。朱安和一位陪伴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女佣王妈相依为命,这笔钱暂时可以勉强度日。但后来随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周作人没有加钱,自尊自爱的朱安也不会开口要他加钱,花与丈夫绝交的二弟周作人的钱她心里极不情愿,但许广平又音信皆无、联系不上,生活费没了着落,当时北平每人每月最低的生活费已经上涨到了六百元,朱安和女佣两个人即使省吃俭用,最低的生活开支每月至少也要在千元左右,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靠一百五十块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霉豆腐等,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到一九四四年积蓄用尽并已经欠债四千多元。
“联准票”一百五十元是什么概念?唐弢后来在《帝城十日》中写道:“我了解到:两位老人(朱安的女佣王妈)每月必需的生活费约合联准票九千元(当时方通用汪记储备银行的‘储备’票,而北方用的是联合准备银行的‘联准’票)……我和哲民去西山时雇用三轮车二辆,每辆车费一百元。如果再将‘联准’票折合‘储备’票,我核计一下,九千元不过买几篓水果而已。”这里可能有两种币值换算的误差,周作人给的这点钱(一百五十元),后来虽不能说是杯水车薪,但维持基本的生活用度,显然已经不够了。出于无奈,这才有了后来的出售鲁迅藏书风波。
2.朱安为什么要售书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鲁迅自一九一二年五月初,随教育部从南京北迁到北京供职,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底离京南下,在北京共生活了十四年,这期间,他陆续购买了大量的中外书籍、碑帖等,这些藏书绝大部分留在北京朱安与鲁迅生活的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旧宅,共计二十三箱又三大书柜。鲁迅去世后,朱安始终妥善保管,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由于生活所迫,社会上传出了鲁迅藏书要出售的消息。
这一年秋天,许广平听人说起上海的旧书铺流传着北平传来的一份鲁迅藏书的书目,经了解得知:北平的书肆来薰阁等将鲁迅藏书中外文详细书目三册传到上海、南京兜售,因索价过高,买主一时未定。许广平知道后心急如焚,决定马上采取措施加以阻拦。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她给中断联系两年多的朱安去信劝阻,信中说:
朱女士:
日前看到报纸,登载《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的消息。此事究竟详细情形如何,料想起来,如果确实,一定是因为你生活困难,不得已才如此做。
……
至于你的生活,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我已经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从没有一天间断。直至前年(卅一年)春天之后,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又汇兑不便,商店、银行、邮局都不能汇款,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平,因此一时断了接济。但是并未忘记你,时常向三先生打听。后来说收到你信,知道你近况。我自己并托三先生到处设法汇款,也做不到,这真是没奈何的事。
鲁迅先生直系亲属没有几人,你年纪又那么大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虽则我这里生活负担比你重得多:你只自己,我们是二人,你住的是自己房子,我们要租赁,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财力,也比我们旁边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
作人二叔以前我接济不及时,他肯接济了。现在我想也可以请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后我们再设法筹还。我也已经去信给他了,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
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
其实想北上的心是总有的,鲁迅先生生前不用说了,死了不久,母亲八十岁做寿,我们都预备好了,临时因海婴生病了取消。去年母亲逝世,自然也应当去,就因事出意外,马上筹不出旅费,所以没有成行。
总之,你一个人的孤寂,我们时常想到的。望你好好自己保重,赶快回我一音。
不知朱安收到此信后做何感想,按常人的理解,这时候的朱安应该对许广平心存抱怨,没有这次“售书风波”,上海许广平方面断绝了与她的联系,已经两年多对她的生活不管不问了。
当时的上海、北平虽然已经沦陷了六七年,但是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真的会没有经济往来、金融往来?连钱款都寄不了了吗?如果真的挂念朱安老太太,两年多时间会音讯皆无?目不识丁、不善言辞的朱安找不到许广平,但三弟周建人也在上海,且与大哥鲁迅一家来往密切。朱安出于无奈,找过周建人,但始终也联系不到许广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许广平真要想联系朱安却易如反掌,寄款也好,问候也好,说明情况也好,一封信就能寄到,老人至死从未搬离过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旧宅一步,许广平当年也多次去过,朱安不识字,但身边还有一些故交旧友帮忙。
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事人所共知,两个人早已情断义绝、互不来往,即便在敌伪时期周作人落水,他再有地位,再有财力,似乎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负担寡嫂的生活。因为此前朱安已将鲁迅的著作版权转让给了许广平,她也没有分得鲁迅死后在上海的遗产和存款,条件是许广平承担朱安晚年的生活费用——生养死葬,而实际上这种许诺并没有完全兑现。
朱安性格温婉、心地善良,不是挑剔多事、斤斤计较的老太太,她可能考虑得不多,但是许广平母子在周家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九三七年春节婆母鲁瑞八十岁大寿、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去世,都没有回过北平,这两年既不寄钱奉养也不寄信问候,这些事实朱安心里是再明白不过了,自尊自强的她没有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寻找许广平讨要生活费,出于无奈,这才有了出售丈夫鲁迅藏书的想法,这才引来了上海方面的及时反应,马上写信阻拦。按常情理解,不卖书不联系,一听说要卖书,马上得到回应,难道鲁迅的藏书比朱安的生存还重要?
许广平有知识有文化,深知鲁迅的价值,为维护鲁迅竭尽全力,同一天,她也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出面劝阻大嫂朱安停止出售鲁迅藏书。
许广平一九二二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一九二四年改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也曾是周作人的学生,与鲁迅结合以后,她了解兄弟失和的事实以及周作人对她不接受的态度,但在抗战结束以前,许广平表面上对老师还是尊敬有加的,她给周作人去信阻拦卖书一事,语气态度还是十分恭敬的。
3.“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十天之后,许广平偕子海婴委托律师事务所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的《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
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有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同时,鲁迅生前好友郑振铎、内山完造等人也极力想办法阻止售书一事,郑振铎托北上的刘哲民和唐弢去面见朱安,并带去亲笔信分致来薰阁、修绠堂等书店老板和赵万里等版本专家,请他们共同出力保护鲁迅藏书,内山完造也给朱安去信加以劝阻。
其实,在接到许广平的信后,朱安得到承诺,已经打消了卖书的想法,她有没有给许广平回信不得而知,但是在接到内山完造的信之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她托人代笔回信,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产生卖书想法的缘由。
内山完造是鲁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在中国居住了三十五年,主要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鲁迅常去买书、聊天、会客,两个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十年间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内山完造与许广平也相当熟悉,两家交往密切,内山的信没有留下,朱安在托人写的信中说:
鲁迅生前,我和我婆母周老太太的生活费,每月提前寄到,过年过节总是格外从丰,并且另有存储一千余元,以备不时之虞,我也克(恪)尽我的天职,处处节省,自鲁迅逝世之后,我秉承婆婆的意思,把储存之款分月拨作家内的家用,当时有一位许寿裳先生,来代许女士索要鲁迅先生全集的出版权,担保许女士嗣后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费,不使缺少,同时许女士也有信来索取版权,并表示极端的好意,我自愧无能,慨然允诺,当将委托手续全部寄去以后,许女士如何办理,迄未通告,我亦未曾问过,到廿八年冬季,因家用不足,我婆婆周老太太函商许女士,请每月酌加二十元,未能办到,以后婆婆的花费,都由周作人先生担任,银钱之外,米面煤炭,常有送来,水果糕点,应有尽有,房屋亦来修过。卅一年五月,并我每月四五十元之零费没有了着落,只好典卖钗裙,黯(暗)自弥补,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周老太太逝世,一切丧葬费用,全由作人先生担任,并仍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实在可感!虽然这点钱仍是杯水车薪,但我也不便得寸进尺,计较盈绌。
生活是飞也似的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余元,这真使我无法周转!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的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版权手续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代许广平找朱安索要的,条件是许广平承诺保证负担北京旧宅婆媳的生活费,不使缺少。鲁迅全集的出版权寄出后,“如何办理,迄未通告”,版税收入多少?如何分配?逆来顺受、忍让迁就的朱安概不知情。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通过和婆母鲁瑞的通信保持着与周家的联系,内容主要是家庭经济和汇报孩子的情况。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物价上涨,年事已高的婆婆鲁瑞去信要求每月增加二十元,许广平未能办到。婆媳之间因生活费问题一度发生冲突,经许寿裳等人从中调停方得平息。按情理讲,母亲鲁瑞的养老问题不应只由大儿子负责,况且鲁迅已经去世,家庭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许广平负担了十四个月之后,鲁瑞的生活费改由二儿子周作人负担。但上海方面理应承担朱安的生活费,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却没有了着落,老人后来靠典卖借贷度日,无物可卖、借贷无门时,自然想到了藏书。
朱安在信里最后写出了她计划卖书的真正原因:“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朱安的这点家务事,明眼人一看便明白她要售书的原因所在——生活所迫,走投无路了!
上海方面在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阻止售书,几天以后,鲁迅的弟子唐弢、刘哲民受郑振铎的委托去北平洽谈生活费的事。
两个人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抵达北平,然后马不停蹄地在“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十九六天,穿梭似的出入各书铺,十四、十六两次到北京(平)图书馆访宋紫佩,十五日清晨八时访赵万里,谈的都是鲁迅藏书出售的问题。”(唐弢《〈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唐弢带着郑振铎写给来薰阁、修绠堂等书店老板及版本专家赵万里的信,请他们阻止鲁迅藏书流散出去。十四日傍晚,唐弢和刘哲民在鲁迅的好友宋紫佩的陪同下到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拜见了朱安。当时朱安正和女佣王妈在吃饭,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碟子里只有几块酱萝卜。听说唐弢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心里的怨气溢于言表。两年多对她的生活不闻不问,听说有售书之举,上海方面动作迅速,马上就派人来了。
唐弢事后在《帝城十日》中记载:“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去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
宋紫佩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最知心的朋友,鲁迅离京后,宋紫佩对鲁瑞和朱安婆媳多有照顾,与她们的关系相当亲密。见到朱安脸有怒色,他马上从中斡旋,说明两个人的来意。唐弢又将许广平和好友对保护藏书的意见补充了几句。老人听了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才冲着宋紫佩大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唐弢等人介绍了上海出版鲁迅全集的情况,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上海书籍抄走,直到导致汇款中断的经过,仔细说了一遍。解释了沪方中断生活费的原因,特别是海婴身体不好的近况。唐弢连忙表示:朱安日后的生活费仍由许广平承担,如有困难,朋友们也会凑点钱让她渡过难关,保证绝无冻饿之虞,鲁迅的藏书是不能卖的。
听到这些,生活费得到了保障后,朱安对许广平的误解渐渐消除,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消。
朱安虽然没有文化,却是心地善良、深明大义、识大体、有主见、有骨气的女性,动议卖书实属出于无奈的个人行为。上海方面中断了两年多的接济供养,无音无信,联系不上;周作人给的钱既不能完全解决生计,她也不愿意接受,生活实在是难以为继,这才产生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动念。
4.售书牵扯周作人
有一些论者认为“售书风波”是周作人幕后指使的,我以为,缺乏令人信服的相关证据,也似乎不太合乎情理。
“售书风波”发生后,许广平也许怀疑过这件事与周作人有关,因为按照常理理解,朱安没有文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与外界很少接触,怎么会想起要出售鲁迅的藏书?在北平的亲友之中,关系最近、经济上有负担,又了解鲁迅藏书价值的似乎只有周作人。
许广平的疑虑有她的道理,但当时只能深埋心中,不能表露出来。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周作人虽然不是君子,在赡养母亲方面做得未必尽心尽力,但实事求是地讲,鲁迅去世后,他在供养母亲和寡嫂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替许广平分担了许多经济压力。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去世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寄北平家中的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由北新书局以版税支付了一年多,其后(一九三八年一月),周作人每月给母亲鲁瑞五十元,许广平每月给朱安四五十元。一九四一年底,许广平被捕入狱,从此音讯皆无,中断了对朱安的供养,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现“售书风波”的传言。一九四三年四月鲁瑞去世前,叮嘱周作人将自己每个月十五元大洋的零用钱转给朱安,让她务必收下,说这是属于她的钱,与别人无关。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朱安的生活由周作人勉力维持,每月一二百元不等,大嫂代他们周氏兄弟照顾了母亲三十多年,他成了寡嫂生活的主要供养人。得罪了周作人,沪方赡养朱安的负担会加重。
其二,许广平的疑虑当时只是猜测而已,说周作人指使寡嫂朱安售书,要拿出真凭实据,哪怕是道听途说的传言也好,这方面她当时没有直接的证据,据她讲是一九四六年去北平时听宋紫佩说的,但那是两年后的事情了。她可以不考虑周作人的人品及当时的地位权势,但无凭无据,实难出口将责任推向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在写给鲍耀明的信中,涉及许广平,这样说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词……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鲁迅生前,许广平虽然知道一些兄弟失和的事,但她在女师大读书的时候,周作人是她的老师,两个人素无意见隔膜,一直保有师生之谊。鲁迅的家事,尤其是兄弟二人都讳莫如深的失和问题,她更不便介入其中。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曾经写信给周作人,托其照顾鲁瑞和朱安,周作人也尽到了一定的责任,她当时有求于人,对周作人还是尊敬的、客气的。当然,许广平也清楚,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和她的结合,认为鲁迅是喜新厌旧,抛弃原配妻子,在他心里,长嫂只有明媒正娶,陪伴、照顾母亲三十八年的朱安,她才是鲁迅的结发夫人,自己的身份周作人是不接受不承认的。
抗战结束以后,周作人因附逆投敌沦为文化汉奸,被视为民族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成了万人捶的破鼓。鲁迅则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广平与周作人的身份境遇发生了天壤之别,她对周作人的态度也变得激愤起来。涉及三十年前的出售鲁迅藏书事件,许广平将幕后的推手归罪于周作人,她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的《北京晚报》发表的《火炬·黎明·旭日东升》一文重提此事,说:
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他借口鲁迅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示别人整理出鲁迅所藏的中文、日文及其他外文书籍,编成书目三期,到南方去出卖。我因开明书店一位朋友的帮助,得知此事,托其借来书目一看,大惊失色,知为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因即设法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
周作人见到报上的文章十分不平,马上写信进行反驳:
七日贵报登有许广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间说及出售鲁迅藏书的往事,辞连鄙人,仿佛说是我的主意,事实有她当年的一封信为凭,完全不是这样的。今照抄一份送上,请赐一阅。据信中所说,自民国卅一年春即不能汇款,以后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给,此为分所当然,说不上什么“鼎力维持”,但是“俾将来继续清偿”,结果却是一番胡来的诬蔑,实真是最可感荷的了。不敢希望玷污一点贵纸的篇幅,只是请你花费些许贵重的工夫,请把那书信通看一过罢了。
此时的周作人处在墙倒众人推、没有话语权的境地,知道即使自己写文章辩解也没有发表的可能,只能抄录许广平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写给自己来信的主要内容做以说明:
日前上海报载,有北平家属拟出售藏书之说,不知是否属实。果有其事,想为生计所迫使然。鲁迅先生逝世以来,广平仍依照鲁迅先生生前办法,按月筹款,维持平方家属生活,即或接济不继,仍托平方友人先行垫付。六七年间未尝中辍。
直至前年(卅一年)春间,身害大病,始无力如愿,病愈之后邮政银行商店俱无法汇款,而平方亦无熟人可托,束手无策,心甚不安。不久前报载南北通汇,又多方设法仍苦无成。其间重劳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
前者出售藏书之消息倘属事实,殊负先生多时予以维持之意,广平特恳请先生向朱女士婉力劝阻,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即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亦先生爱护先贤著作之意也。
至朱女士生活,广平当尽最大努力筹汇,如先生有何妥善方法示知更感。倘一时实在无法汇寄时,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接济款项亦盼示知,俾将来陆续清偿,实最感荷,先生笔墨多劳,今天以琐屑相烦,殊深感愧,尚祈便中赐教一二,俾得遵循。
许广平在信中承认:自己接济不继时,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生活费以后“实在无法汇寄时,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接济款项亦盼示知,俾将来陆续清偿”。让周作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自己当年勉力维持孤母寡嫂的生活用度,不求回报,不可能开具款项的明细,也从没指望许广平日后偿还,事实上也从未偿还,没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胡来的诬蔑”。
5.许广平的回应
周作人的来信及抄件很快转到了许广平手里,她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致《北京晚报》记者的信中,做了回应。信中说:
转来周作人信,知此汉奸年老仍火气十足,希免其罪恶之责,而来信未能一语反驳其出售藏书之事。这事乃一九四六年我到北京时,见了宋紫佩先生,亲自告诉我周作人如何下令馆员整理书目情况(后来,周作人迫他认其私宅偷盖房屋而要他[宋]认是公账。即有通同作弊之嫌。宋愤而生病,致双目失明,现已死)。宋当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情况不会不确。后见朱女士(鲁迅前夫人)亲手交出整理书目三本(现存鲁迅博物馆)。我当即劝她保存遗物,并允负责其生养死葬,立有合同,以防周作人家属挑拨发生问题。这些都有文件在博物馆内。
当然,从我写给周作人的信(来信附来的)看出,我那时听说出售藏书,明知是他所为。朱女士目不识字,如何能策划图书馆人来给她服务呢?事实了然,后面主使即是谁。我苦心孤诣,写这封信去,说明请他暂为垫付,以后陆续清偿。他却并无清单寄来,我自无法清偿,现在仿佛是我“胡来诬蔑”。
……
至于老母寡嫂生活,事实是一九三六年鲁迅死后,每月由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到“八一三”抗战起,即行停付。战争期间,我即托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李霁野先生按月垫给朱女士五十元(这之前,我因儿子身体多病,经朋友介绍,想到南洋工作,要离开上海。曾有信给周作人,托其照顾北京家属。经其回信,说母亲他可以负担,朱女士则不管了。我才无法,转托李霁野先生,每月筹寄五十元的)。后来,北京沦陷,上海亦成孤岛,李霁野逃离南方,我又被人拘禁,就听说有北平(旧称)出售藏书之事。由来薰阁人亲自带至南京,陈群看了书目,全部包下,但来薰阁负责人忠于周作人,望在上海得更高价,才到上海向书肆兜售,我才得知。观我给周作人信中所说(你们转来的),实千方百计想对北京家属负责,而不是如他所说“胡来的诬蔑”的那样子人物。
这封信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
其一,许广平说周作人指使北平图书馆工作人员整理鲁迅藏书书目,以利销售一事是听宋紫佩说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底,这个月的二十四日她到北平住了半个月,为整理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此时的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宋紫佩就在北平图书馆工作,他与朱安相当熟稔、亲近,时常问候看望,朱安要整理书目完全可以直接让他找人帮忙,何必通过周作人另找他人。不管宋紫佩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愤而生病,致双目失明”,但人已亡故,查无对证,只能说是许广平的一面之词。
其二,称朱安为“鲁迅前夫人”是不准确的,朱安始终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两个人从未解除过婚约,无所谓前后之别,朱安虽然名不副实,许广平也不能以实代名,否认事实。鲁迅逝世后不久,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特意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
许广平当时在接到许寿裳的信及年谱草稿后,认为:“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她希望许寿裳将“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就直接改为“与许广平同居”即可。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广平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鲁迅当之无愧的夫人,朱安的身份极少被人提及,许广平称她为鲁迅的前夫人,是否是为了自己正名?置事实于不顾?至于劝朱安“保存遗物,并允负责其生养死葬,立有合同”之事,是在“售书风波”之后的补救措施。此前,鲁迅去世后遗产、版权问题,朱安已全权委托许广平负责,其条件就是许广平负责她后半生的生活保障,但事实上不管是什么原因许广平并未完全兑现,这才致使朱安难以生存,萌生了出售藏书的想法。
其三,关于鲁瑞及朱安的生活费问题,许广平让周作人“暂为垫付,以后陆续清偿。他却并无清单寄来,我自无法清偿”。这根本就不成为不还钱的理由,在周作人看来,抚养老母寡嫂是分内之事,理所应当,并非垫付,也没想过事后让人偿还。但是作为许广平,既然当初承诺过,人家不寄清单来就能成为不清偿的理由吗?事过三十年,主动联系过吗?还过一分钱吗?找人借了钱,事隔多少年没还,反赖债主子从不逼债讨债,这道理讲得通吗?
其四,从上海沦为孤岛到北平计划出售鲁迅藏书之事,其间两年多中断了对朱安的供养,许广平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没有断供的前因,何来藏书拟售的后果?售书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引来了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应,邮路也通了,钱款也能筹措了,人也能联系上了,老太太的生活费这才有了着落,当然,前欠了两年多的钱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事论事,周作人政治上有污点不假,附逆投敌,罪不容赦,但不能就此将他一棍子打死,不顾事实,没有根据,硬将“售书风波”和周作人绑在一起。
6.周作人是幕后推手吗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有类似记载,他的观点显然也是受母亲许广平的影响。
周海婴说:
当时许广平从朋友处听说,上海的旧书铺子接到传来的一份书目,说是周作人要卖鲁迅在北平的藏书,书目有一册厚。许广平一听几乎昏了过去。母亲为了保护父亲鲁迅的文稿、遗物,宁愿坚守孤岛,备受日寇凌辱迫害,而身为胞弟的周作人竟要毁掉鲁迅遗物中重要的部分——藏书。许广平当即托朋友打听详情。
两三天后,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因沪京两地战乱汇兑难,北京朱安女士手头拮据,生活有困难,理所当然要向小叔子周作人暂借些柴米钱。周作人竟借此怂恿朱安卖书,让北京图书馆的几个职员清理鲁迅藏书……因索的价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不然北京的书肆为何不马上一口“吃”下来?显然,这书价必是内行的周作人开的。……不久又传来:在售书目录里,有若干善本古籍,已被周作人圈掉占为己有。
母亲的另一想法是托北平的老朋友去劝阻朱安女士,同时急筹一笔钱送去,解除她眼前的困难,以此釜底抽薪之法使父亲的北京藏书不被变卖,周作人的招术才会落空。……而此时,周作人却过着拥有多个佣工、管家、车夫的上层生活,与之相比近在身边的嫂嫂所过的日子差别是多么悬殊!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且又(有)了我,对此周作人及其日本老婆并不承认,并视之为仇敌……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把其视为“正宗”的嫂子朱安好好供养起来,况且她还与我祖母一起生活,这才顺乎其理。再说,当时周作人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偏把朱女士的生计推给远在上海的我的母亲来承担,而母亲抱着我这个病孩……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说法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要顾及事实。
朱安生活难以为继,大哥去世,三弟周建人远在上海,经济支绌、能力有限,朱安替周作人分担了照顾母亲的义务,他力所能及地关照寡嫂的生活也是应该的,但周母已经过世,朱安的晚年生活出现困境,主要责任人不是周作人,应该是许广平。鲁迅在上海的遗产和著作版权全权交给了许广平,朱安的生活费按理就应该由她负责,当时有委托书、书信和证人,即使许广平一时接济不周,向小叔子周作人暂借些柴米钱怎么能说是“理所当然”呢?
周作人过什么样的日子、能力的大小、如何供养母亲、家里有多少佣工、管家、车夫,那是他自己的事,与许广平母子无关。问题在于,作为小叔子的周作人没有抚养嫂子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从情理上讲,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代丈夫尽孝,服侍老太太鲁瑞三十八年,也减轻了其他两个儿子的负担,周作人对嫂子朱安有所付出并非不可。但因为还有许广平,她和朱安属于一家人,更应该休戚与共,关心照顾,尽力负担朱安的晚年生活。从法律的角度讲,鲁迅在上海的遗产由许广平继承,朱安不仅未分到一分钱财产,还将鲁迅的著作版权委托给她。两个人有文字约定,有中间人作证,许广平应该信守承诺,在经济上承担供养朱安的义务。当然,我相信,当年的许广平的确也是困难多多,经济上捉襟见肘,力有不逮,但是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说周作人怂恿朱安卖书,让北平图书馆职员清理藏书,周作人开书价、占有善本古籍等似乎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许多论者将售书事件归罪于周作人,基本上都是源于许广平的说法。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周作人是否与此事有关。
出售藏书的直接诱因是家庭经济问题,是没有生活来源的朱安想将藏书出售以换取必要的生活费。
鲁迅北京的家属生活困难发生在母亲鲁瑞去世以后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底,这之前,朱安和鲁瑞的生活费由代表大儿子鲁迅的许广平和二儿子周作人共同负担,理论上是周作人负责鲁瑞,许广平负责朱安,各出五十元,维持鲁迅生前原来的水平。其间,自一九四二年五月许广平失联,孤母寡嫂只能由周作人勉力抚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至少供养朱安的义务应该是许广平,而不是周作人。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好与坏,社会地位高与低,也无论他家里雇着多少佣人,都没有义务负担嫂子的生活费,况且他和鲁迅早已手足情断。周作人虽然对兄长无情无义,但对大嫂朱安却始终是尊敬的、关照的,说他为了减轻负担,怂恿朱安出售鲁迅藏书,要有真凭实据,否则,难以服人。
况且,一个目不识丁、无儿无女、生活无着、孤苦无助的老太太,卖掉亡夫的藏书以求生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鲁迅还没有被神化、被政治化,朱安不可能认识到丈夫的价值、丈夫藏书的价值,周作人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一起长大的大哥的重要价值。即使当时鲁迅已经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妻子打算卖掉丈夫的藏书以维持生计,也是情有可原的无奈之举。鲁迅是名人不假,但名人的原配夫人穷到了要饿肚子活不下去的地步,用名人丈夫的遗物获得生存的权利,这正符合鲁迅的观点:“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周作人夫妇承不承认许广平母子的地位,以及他经济能力的大小,都与他供养寡嫂没有必然联系,还是那句话,他没有这个义务!朱安是有条件地放弃了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力,受益者应该有所付出,保证她的晚年衣食无虞。
“售书风波”只是一场风波而已,正是因为有了这场风波,失联两年多的许广平才重新出面找到朱安,才重新负担起她的生活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得不到赡养的朱安晚年才有了起码的生活保障。
“售书风波”的起因是生活困难造成的,许广平有一定的责任,它至少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朱安作为鲁迅的“遗物”也是应该好好保护的!周作人很可能认识不到鲁迅藏书的价值,但说他背后指使出售、企图占有这些藏书,没有确切的证据,既然拿不出真凭实据,就不能硬将“售书风波”与周作人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