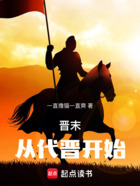
第9章 寒冬雨夜,镌刻留名
“道友,刚才可是绝佳机会!”难民中有人低语。
居于人群中央的一人,压着声音开口:“不可打草惊蛇,孙仙师已准备今夜子时攻城。既然我等已由暗道潜入这城中,只需静待即可。介时里应外合,必能破城!”
又有人提醒道:“适才那骑马的一人,似乎已发现我们。”
中间的人又皱着眉,回想了一下,摇摇头:“是你看岔了,那公子哥哈欠连天,怎会留意到这里。况且我们穿着破烂,狗官们看到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哪会想那么多。”
提醒的那人有心再说什么,却被边上人拉住,只能作罢...
谢混这边,不疾不徐骑着马,与桓宝等人行至拐角处。
待众人转过弯后,他招呼桓宝、刘穆之,示意附耳说话。
“桓将军,立即派人查探城中可疑人员,半个时辰后,我要知道具体数量!让城防军随时待命,准备拿人!”
“穆之,你即刻出城通知蒯恩他们,留五百人在城外戒备,其余人回城救援!”
两人听到这话,眼神惊骇。
城中可疑人员?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更遑论,一个是刀尖舔血的将军,一个是聪慧过人的幕僚。
一听就懂。
“谢长史确定?!”
桓宝神情严肃,确认道。
刘穆之也一脸郑重。
“确定!事情紧急,本官命你二人立即去安排!不得有误!”
谢混强势下令。
“是!”
...
半个时辰后。
一千城防军着甲待命,另有两千人分散把守各个城门、要道。
蒯恩、到彦之领着一千五百人于城外等候,随时准备进城。
檀氏三兄弟带着五百人,以防意外。
为避免混入城中的人狗急跳墙,郡府对外宣称是新来的长史,要在城外曜兵。
“禀报谢长史,城中贼人数量已探明,请过目!”
郡督邮陈昌将一叠纸条递上。
这是多个探子的密报,陈昌不敢耽误,第一时间就送来了。
谢混接过,越看越心惊。
足足一千五百余人混入城中,分别聚集于三个地方。
“干什么吃的,一千多人进入城中,你们居然毫无察觉!”
谢混忍不住暴怒拍桌。
顿时,茶水四射,溅了一地。
孙恩大军少说几万人,加上这一千多人里应外合,句章必会城破。
在城中的他,也插翅难逃。
人死如灯灭,他的宏图霸业亦是空谈。
即便侥幸活了下来,在朝廷那里,也要得个御敌不力的罪名。
桓宝、袁崧、陈昌等一众官员将领,噤若寒蝉。
这个罪责,没人愿意担。
谢混压下怒气,再次开口:“他们是如何进城的?!”
陈昌脊背有些冒汗。
未曾想这长史看着俊雅,发起火来,居然如此慑人。
他战战兢兢回道:“据探查,是自城墙下挖暗道,通至几户农家后,进来的。”
尽管现在是紧急时刻,但谢混听后,仍旧忍不住要收拾人。
“好得很,眼皮底下都被人钻进来了。给我将负责巡防的郡尉、贼曹掾史,立即革职下狱!”
陈昌不敢应话。
这两人,一个分属袁崧,是其侄,另一个分属桓宝。
他都不敢动。
见陈昌半天没反应,谢混气极反笑:“怎么,我这长史命令不动你?”
陈昌小心翼翼瞄了瞄桓宝和袁崧,见这两人垂眉低首的模样,他忍不住暗骂了一句。
他只是一个小小督邮,居然要夹在郡太守、广武将军、军府长史中间,承受他不该承受的重。
谢混当然知晓陈昌为什么犹豫,他冷冷逼视桓宝和袁崧:“如今贼人就在城中,耽误军情,别怪本长史翻脸不认人!”
片刻后,袁崧率先承受不住压力,悄悄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对陈昌道:“快按谢长史说的,去将袁成拿下。”
桓宝见状,也只能对身后一人吩咐:“你随陈昌同去,将严民拿下。”
那人踌躇片刻后,才与陈昌一同离开。
谢混眯了眯眼。
瞧着这些人的反应,看来他动的这两人,关系不简单。
随即,他暂时将此事抛开,把密报递给桓宝,下达军令:“桓将军,命你领一千城防军,即刻前往这三处剿灭贼寇。袁太守,派人赶往北城门,迎蒯恩他们进城协防。并派探子严密注意城外,谨防孙贼!”
...
随着谢混军令下达,一众将士各司其职,城中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
有察觉不对的贼寇,率先钻洞跑出城,不过被蒯恩布设在城外的人马,逮个正着。
一刻钟后,一切就绪。
半个时辰后,纷乱平息。
桓宝、蒯恩、到彦之拢共剿贼一千余人,生擒五百。
谢混把这些人,全安排去加紧修筑防事,并告诉监守士卒——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敢跑?
就地处决!
这五百人与被裹挟的百姓不同,乃是孙恩的忠实信众,谢混自然对他们狠。
在这群人中,还有几个骨干成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谢混从他们口中得知——今夜子时,孙恩将进攻句章城。
...
当夜,下起濛濛细雨。
谢混站在城墙上,静待贼寇。
在得知孙恩即将来袭后,他便与桓宝、袁崧等人,议定了布防。
如今蒯恩、到彦之、桓宝等人已带领五千士卒,全部就位。
檀氏三兄弟也领兵五百,埋伏在城外林中。
袁崧率两千人,镇守于西南面百米外的姚江渎垒上。
考虑到孙恩是子时进攻,视线受到极大限制,为此,谢混特意命人特意赶制了很多弩箭和箭矢。
一只冷箭,便能收割一条性命。
没有比这更划得来的了。
城内安置了投石车,一颗颗巨石,放在一旁。
金汁、石灰罐也准备不少。
此乃大杀器。
这时候医疗条件差,一桶金汁下去,只要被烫伤感染,断无活命的可能。
石灰罐也一样,不慎入眼,直接眼瞎。
很快。
子时!
孙恩贼军分水、陆两路进攻。
陆地上。
由他亲自披挂上阵,领一万多主力,推着攻城车和投石车、云梯,从东面进攻。
两侧各有五千余众,进攻西、北两面。
水路上。
卢循率领三千水军,自大浃江入姚江,准备在句章城南面登岸。
随着贼寇挺近东、西、北三面城下,喊杀声也近在耳边。
东面城墙上的蒯恩,北面的到彦之,西面的桓宝,立即下令。
“杀!”
“全力杀敌!”
士卒拼命张弓搭箭,根根箭矢发出,盲射城下黑暗处。
同时,桶桶滚烫金汁,倾泻而下。
城内也开始抛射巨石。
伴随着的,是城下声声惨叫。
一时间。
贼寇死伤惨重。
但孙恩信众悍不畏死,登云梯、投石车、攻城车,齐上阵。
“孙仙师,情况不太妙,句章城好像早有防范。”
一名信徒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跑到孙恩面前,大喊。
孙恩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恶狠狠道:“怎么回事!城内的人呢?!”
“不清楚,已派人摸去暗道通知了!”信徒一脸惶恐,生怕孙恩暴起将他砍了。
“报!仙师,派去暗道的人,皆有去无回,恐官军在暗道对面守株待兔!”又有信徒来报。
孙恩闻讯大怒,由暗道进去的一千余人,是此次攻城的致胜关键。
他之所以分兵四路,是想着分散句章城中兵力。
埋伏于城内的人,趁乱不管打开哪个方向的城门,他的人都能第一时间进入。
如此,句章城便破。
而现在,不但城中埋伏的人杳无音讯,就连句章城防也早有准备。
箭矢、金汁、巨石异常足备。
徐道覆听到后,喝问:“其他两路呢?卢循领的水军如何?!”
他急切想知道,其他几路情况。
但句章城巨大,城围足足八里,单边亦有两里,其他方向的军情暂未传至。
徐道覆没得到回复,立即对孙恩建议:“灵秀,如今官军有备,我方计谋被破,不若引兵退去,保存实力!”
盛怒的孙恩,断然否决:“不行!至少要等其他三方情况传来。”
随后,他大喝道:“现在听我号令,继续全力攻城!”
贼寇骨干闻讯而动,开始传令各处。
顿时,防守东面的城防,压力陡增。
城墙上。
蒯恩手持宽背大砍刀,一刀将一名先登的贼寇,枭首。
血溅了他一脸。
但他根本顾不上擦拭,因为旁边还有数个贼寇已然冒头。
“唰唰!”又是两刀。
两名敌寇俯首。
没人能承受住他一刀,挨上便是断臂、破颅。
“报!蒯将军,敌军主力忽然猛攻,城防快支撑不住!”一名营长急报。
蒯恩顺手又砍杀一人后,喝道:“马上去向谢长史禀报!”
营长领命来找谢混。
谢混和刘穆之一直在东面坐镇,知晓这面是敌军主力。
刘穆之拱手献策:“主上,情况危急,宜命西北分兵支援,并令城外部众突袭!”
谢混也顾不得那么多,果断命人前往到彦之、桓宝那里,传令他们分兵过来。
同时,让人点燃篝火!
“大哥!主上发信号了!”
一直藏于城外林中的檀道济,看到城墙上的火光,急忙告知檀韶。
“众将士听令,随我杀寇!”
一声大喝,檀韶、檀道济、檀祗三兄弟立即率兵杀出。
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孙恩兵众后方。
军队后方、侧面为死亡区,没有哪支军队在被绕后时,还能不溃。
孙恩组织的贼寇只是寻常庶民,一群乌合之众,并且此时夜黑雨稀,在听到后方呼啸的喊杀声时,这些人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直接溃散。
似瘟疫扩散一般,连带着进攻西、北两面的贼寇,也溃逃而去。
“退了!贼寇退了!”
“贼寇退了!”
“我们胜了!”
士卒们狂喊,发泄心中喜悦。
此时,恰好到彦之、桓宝赶到。
谢混当即分别下令:“穆之,你带人清理漏网之鱼。到彦之、桓将军,随我出城追击!”
不过,他有意控制追击速度,这个时间点可不能把孙恩给逮了。
待追出里许,便立即转道,支援南面。
南面渎垒。
防守在这里的袁崧,一直谨记谢混命令,只用箭攻。
只要卢循船只靠近垒边,想登岸,便是一轮强势箭射。
若发现敌人攻势凶猛,便辅以弩箭。
因此,卢循一直被压制在姚江上。
待谢混率军赶到时,卢循意识到其他路已败,便命人驱船逃离。
袁崧想请领水军追击,被谢混以“寒冬雨夜,谨防敌军设伏”驳回。
...
翌日,云收雨霁。
句章城外,到处是贼寇死尸。
至于城墙上的尸体,已被士卒抛下城去。
“主上,此次守城共歼敌七千余人,我方伤亡三百余人。俘虏一千余人。”刘穆之兴奋地向谢混汇报此次战果。
这是大胜。
当然,这些贼寇都是愚民,未经过正规训练,加上句章城准备充足,有此战绩很正常。
“着令,立即挖坑掩埋尸体,俘虏押去服徭役。抚慰伤残,犒赏三军,并于郡府门前立碑,亡者,镌刻留名!”
随着谢混这声令下,众将士哗然。
甚至刘穆之也不禁心颤。
立碑镌刻留名!
这是多大的荣耀。
只是一场寻常城防战,就能得官方认可,名流千古,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一刻,在一众将士眼中,谢混发着光!
很快。
当日下午,一座巨石丰碑便立于郡府前。
一众百姓聚集围观。
忽然,一名年轻女子扑到石碑前,嚎啕大哭:“王郎!王郎,你看到了吗,长史为你立碑了!”
一老妇,泪眼婆娑抚摸着一个名字:“我儿啊!你怎么忍心丢下为娘!”
又有孩童哭泣:“爹,爹!你去哪里了,我好想您!”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伏于碑前痛哭。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
见到这一幕,蒯恩、到彦之、檀氏兄弟,面有戚色。
已为人父的刘穆之,眼角有些湿润,他喃喃自语:“公子真有大德也。若有朝一日,我也会如此悲痛欲绝吧。”
不远处,桓宝与袁崧并肩站立。
良久后,袁崧忽然叹了口气,心生感慨:“咱们这个长史,有些特别啊。”
他想起不久前,谢混曾专程找过他,要求为难民搭建窝棚。
如今又为阵亡士卒立碑。
在这大晋诸多士族中,他不要说见,连听都没听说过。
桓宝沉默片刻,微微颔首。
尽管他因亲信被革职下狱,对谢混有所不满,但同为军中人,谢混善待士卒的做法,还是赢得了他的敬意。
当然,有些东西,并不会因为尊敬而收敛。
“袁太守,如今贼退,我想...你我二人需合作一番。”
“哦?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