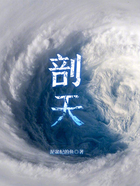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10章 风暴潮(三)
当陈相第三次伴着嘈杂的电话铃声醒来时,终于不再激动地喊妈。
自然之灾面前,人总像秋日的落叶那样脆弱不堪,他们只能在照常普照的阳光下,悄无声息地落地,默默等待粉身碎骨的结局。
死亡的实感仍旧历历在目,此时的陈相正无法控制地周身颤抖,仿佛置身于一个冰罐。
他无法得知是什么让他回到出生的前一天,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年代,和熟悉却又古怪的人打着无厘头的交道,重复经历无法抵抗的灾痛。但有一点他十分确信:
如果他不能尽快挣脱1995年的一切,那么2021年张瑾玥就会和刚刚的他一样被闷在冰冷的海水里,做着或温暖或绝望的梦,渐渐窒息。
天降的劫难无法扭转,但至少还有机会躲避。如果是张瑾玥的死将他困在这时长为4个小时的时间囚笼里,那么提前救下她也许就是打开笼门的钥匙。
于是这一次,他在漫长铃声的尽头拾起话筒,竭力压制住颤抖的声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瑾玥,我有急事找你,在家等我。”
干脆利落地挂掉电话,他转身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勇伸出一只手,“我需要那辆生锈二八大杠的钥匙,还有你的手表。今天晚上有台风和风暴潮,跟任天富说一声。帮个忙。”
张勇的那块万国牌追针计时表看起来就价值不菲,戴在手腕上沉甸甸的。现在是晚上10点半,按照前两次的记忆,台风至少在一个半小时后才会影响到湛江,两个半小时后才会正式登陆,三个半小时后,风暴潮才会来临。即便走广州湾大道回家是绕了个大远路,两个小时也足够了。
这次来得及。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楼,推出车,骑行在半嵌入大大小小石子的水泥路面上,传动系统发出的尖叫和中轴的嘎吱声像交响乐一般热闹。不一会儿,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彻云霄。
“你干什么?”陈相单脚撑地,冲一下子从树丛里闪到路中央的赵栋梁惊呼。他险些撞到眼前的人。
“当班时间你去哪里?”赵栋梁问,语气里满是疑惑。
陈相望着面前怀里抱着本书、满身潮呼呼的人,也同样疑惑地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怕被蚊子抬走吗?”
赵栋梁漫不经心地用书脊扫掉身上还没被布料吸收的水珠,赌气一般地答:“我又不当班,不归你管理。”接着,他走上前一手拉住车把,“你跟张台请假了?”
“请了请了。”陈相连连应和,踩在踏板上的脚开始发力。他想以最简单的方式把赵栋梁打发走。
赵栋梁像是没料到陈相的回答一样,愣了一下,拉车把的手逐渐松开。这让陈相松下一口气。
当嘎吱声再次响起时,陈相身后传来任天富带着喘息的叫喊,“波哥,有台风和风暴潮是什么意思?你去哪里?”
陈相没有停下,只是同样扯着嗓子喊:“明天凌晨1点台风2点风暴潮。台里交给你了,你嫂子有事,我要先回家——”
车子滑下最后一个下坡,即将右转驶离气象台的大门,猛然间陈相察觉到车轮子后面似乎始终缀着吃力的脚步声和剧烈的喘息。刚要转头查看,身后便传来赵栋梁的嘶吼:
“你停下!”
“张瑾玥怎么了?”
“瑾玥怎么了?”
陈相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停下,反而骑得更快了。他始终朝着刮湿风的东方前进,经过扬灰的土渣路和熟悉的葎草地,忍着脚踝上的刺挠把快要散架的车子拖上广州湾大道半人高的路基,一边用衣角抹干净手心上的锈迹,一边冲着在月光下泛白沫的海岸线喘气,半晌才吐出一句憋了很久的话:
“你没必要知道张瑾玥怎么了。你不配。”
赵栋梁对张瑾玥不好,打记事起,陈相就这么觉得。虽然吵架冷战家庭暴力一次也没有,但他总觉得,那两个人的关系奇奇怪怪的,一点也不像夫妻。
张瑾玥在一家小学里管理财务,工作较为清闲,包揽下所有家务,对待赵栋梁也一向热情和周道。
她总是做赵栋梁喜欢吃的鱼香肉丝和西红柿炒蛋,在赵栋梁上长白班时特意等他回家再吃饭;她会在赵栋梁进家门时接过他的提包,把拖鞋从鞋架上取下来正放在他脚边;她会对他嘘寒问暖,心疼他工作忙、夜班累;她为他洗脚。
夫妻之间,本应如此。当山盟海誓的浓烈感情被琐碎的生活冲淡,只剩下互相扶持的责任和义务,这很正常。但是,张瑾玥的付出,始终是单方面的。
作为相濡以沫的伴侣,赵栋梁对张瑾玥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回应。
当张瑾玥伺候他时,他总先是摆出一幅受宠若惊的忐忑样子,然后恢复一成不变的冷脸,最终眼神飘忽不定地安然享受。
他从来都不过问张瑾玥的生活,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不为她过生日,不帮她操持家务。在还没有通燃气的时候,家里的液化气罐是张瑾玥自己搬的,老化爆裂的水管是楼上王奶奶的儿子修的,台风天之前屯菜买得太多提不动是于婶帮着送回家的。
也许在赵栋梁眼里,家就像酒店,张瑾玥就像服务员。
有些家庭里,由于经济收入差距悬殊,夫妻双方必然有一方需要成为家庭主妇或主夫。可陈相的家庭也不属于这种情况,在赵栋梁评上高工升上台长之前,工资不比张瑾玥高多少。
张瑾玥在陈波离世之后火速改嫁赵栋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赵栋梁不配。
当从额头上不断滚落的汗珠终于不再因为混入灰尘而蛰得眼睛睁不开时,陈相把自己从飘散的思绪里抽离,扶起车子,继续上路。
他和张瑾玥互为唯一的亲人。他要救她。
夜里12点,湛江市气象台的值班室比以往的任何一晚都要热闹。任天富坐在陈波的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抓耳挠腮,其余人整整齐齐围在他身边。
屏幕上最大化着一张残缺的卫星云图,以120度经线为界,左边全黑,右边亮到险些看不清云体和海面的界限。在明亮的那一半上,显示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上有小半个浑圆的云团,看起来像气旋。
“富哥,到底有没有台风?”张勇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左手捏着自己的右手腕,那里骤然减少的重量让他很不习惯。
借给陈波的手表,是他最喜欢的一块,有当下最先进的追针计时技术。追针秒针重叠在主时指针上方,可以单独行动而不影响主时针,让使用者在一分钟内对两个时间进行精确至秒的记录。
这块表是品味的象征,能把他和戴金色劳力士的暴发户区分开来,吸引到真正的气质女,比如林芳那样的。
“你都问我几百次了?我再告诉你一遍,有,明显有。这9点半的图上都显示有,我也拜托张台请示过上级了,这是今年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第2个台风,内部编号9502。”任天富说完叹出一口气,又刷新了一次窗口。
“那它到底来不来咱们这里?”张勇表情木讷,语气机械。
张勇是被分配来见习的,家人都住中山,正在五桂山上旅游。即便大学四年里去舞厅的次数比去教室的多得多,他也能知道,风暴潮这种东西,比海啸的能量小多了,一遇到大地形就熄火,跟他没关系,跟他家人更没关系。
他只想早点睡觉,平安熬过没剩几天的见习期,拿到毕业证,和林芳一起成为金贵的本科毕业生,跟这个穷地方说再见。
“我觉得不会。你看之前的云图上,副高东撤并且很弱,这种情况下,台风不容易往西走,之前也一直往北。而且咱们这里陆上有稳定高压,就算想来也会把它给挤走。”任天父一板一眼地说。
“那你紧张什么?”张勇把视线移到任天富的右手上,那只青筋暴起的手不断点着鼠标左键,动作快到像要抽搐。
“昨晚9点半不来不代表今天1点不来。风云天气,瞬息万变。”任天富终于被耗尽耐心,松开鼠标把手重重捶在桌面上,“小日本的东西,真不靠谱!”
“嗟来之食,摇尾乞怜,皆是贱格。”远远站着观摩的赵栋梁也开始变得躁动,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回到自己的工位,抽出一本书,转身面对任天富,哗啦啦地翻着。
“就你有骨气你清高。有种你谁的数据都不靠,自己预报。一个神棍。”张勇听清了赵栋梁的话,不由自主地讽刺。
整个气象台里,张勇最看不起赵栋梁。祖上三代都是富商,他自然在看人待人方面颇有天赋。虽然深谙世俗的那一套,但他从不功利和势力,一个小破气象台里也没有值得他功利的人和事。
他一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专业不好就从不在预报天气这事上大放厥词,端茶倒水跑腿吹水,积极发挥能力之内的价值。不像赵栋梁,工作多年没一点成绩,还特把自己当回事。如果不是陈波带头哄着他,估计早就被视为透明人了。
赵栋梁显然不是很服气,他把手上的书往桌上一扣,直视张勇,“我是神棍,陈波就不是了?他撂下一句没来由的话,我们就要忙活一整晚。凭什么?”
“凭我波哥预报竞赛第一,凭我波哥是首席,凭……”
张勇反驳的话只说了一半,便被“咣”的一声巨响打断。值班室的门被风吹开了。
当呜呜的风不断灌入袖口,把被汗水浸润紧紧黏在皮肤上的布料剥离开时,陈相终于迎着压顶的乌云,骑行到二横巷附近。
这一程虽然辛苦,但整体还算顺利。时间指向12点30分,根据记忆,这个时候台风才刚刚靠近,他只要向于婶借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载着张瑾玥往西边随便走几公里,便可以躲过对地形十分敏感的风暴潮。
这次来得及。
二横巷的样子与他童年记忆里的相差不大。潦草的青石板路窄窄的难以双向过车,路两旁挤满低矮的瓦顶平房,杂乱的电线松松垮垮地从布满霉渍的青砖墙间穿过,偶尔在被油烟熏黑的屋檐下缀下一盏昏黄的灯。
夜里,所有店铺都紧闭大门,一扇扇被桐油强行提亮的腐朽门板后,有的溢出淡淡光亮,有的没有。路面湿漉漉的,车轮轧在上面发出粘腻的声响,不小心骑到翘起的砖面上,车铃都被颠响。
这里的夜晚向来寂静,还好有愈加狂暴的风声掩盖,老旧自行车的独奏曲并不那么刺耳。陈相轻车熟路地拐进一个无灯的、只容一人通过的窄巷,那里坑坑洼洼漆黑一片,但他通过得既快又顺畅。这里是他生活了18年的地方,他闭着眼睛都知道该在哪里转弯。
不一会儿,他终于到达目的地。红砖砌成的院墙包裹着四栋三层高的平顶小楼,外墙上刷的红漆还很新,在路灯下反射出水渍的光亮。楼间被粉煤砖砌成的简易花坛隔开,花坛里种着形形色色的植物,其中要数花椒树最显眼,疙疙瘩瘩的树枝疯狂摇晃,在路灯下投出张牙舞爪的阴影。
他把车子停在花坛边,跑向院角的一栋,大踏步迈过矮矮的两层台阶,扑向楼尾的一扇刷红漆的铁门。
“瑾玥,开门。”他边砸门边喊。
门旁边的小窗紧闭着,屋内的光亮被蓝色的薄布窗帘遮挡,比忽明忽暗的路灯灯光更加柔和。他望眼欲穿地期待张瑾玥的身影,可惜没能如愿。正要想办法破窗时,二楼的开放走廊里传来吱嘎的开门声。
“陈波?你没带家门钥匙?”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什么也没摸到。于是后退两步,仰头看见头发还是全黑的王奶奶扶着半墙冲他探头。现在她是王阿姨了。
“哎呦,你怎么满头大汗浑身湿刮刮的?快快上我家里来换一件,我家冬冬的衣服你能穿。你家瑾玥我晚上收衣服的时候遇见她了,说是要到小卖部给你打电话。一去去好久。”
眼前的王阿姨顶着蓬乱的头发,眯缝着眼睛,语气里满是被扰了清梦的不耐烦,却一直说着关切的话。这让陈相心中升起一股暖意,像是回到了被张瑾玥摇着扇子哄睡的小时候。
“姨你看见瑾玥回家了吗?”他追问。
“没有。你家里一直没动静。”
头顶的话音刚落,天上落下密密匝匝的雨滴。陈相转身小跑两步扶起自行车,踩着踏板准备脚下发力时,扭头对还站在原地的王阿姨喊:“姨,一会儿刮大风下大雨还要涨水,你让冬冬弟弟带你往西边去躲一躲。”
哗哗的雨声中,自行车吱的嘎声听不清了。陈相原路返回,穿过已经积上水的窄巷,来到巷口的小卖部。门头上的“二横小卖部”没有被灯珠照亮,两扇木门紧闭着,锈迹斑斑的铁挂锁被风吹得咯噔响。
正当陈相准备再次砸门时,用余光瞥见不远处还亮着招牌的店铺前,弯弯上翘的屋檐下,站着一个双手举伞的人。伞下,宽大的连衣裙裙摆被风吹得一直飘。直觉告诉他,这是张瑾玥。
没有忐忑,没有激动,没有五味杂陈,当他一路小跑过去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脸时,心中只剩下焦急。
1点多了,即便这里不如海边开阔,风没有大到能把人钉死在树上,如此之低的地势也注定无法逃脱风暴潮的魔爪,更何况这里还临近南桥河。
南桥河是湛江最大的一条泄洪河道,与同为泄洪河的北桥河共享一个入海口,如果水位暴涨决堤,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波?你回来啦。”张瑾玥看到眼前的雨人,本能地把伞往前递。
陈相接过伞,迎风撑好,一手揽着张瑾玥调转方向,脚步匆匆地走,“瑾玥你听我说,这里马上要发洪水,咱们到西边躲一躲。”
张瑾玥没有做声,只是默默跟着。两人贴着沿街的铺面走,走在高高低低木制台阶上,避免了脚下的滑腻。
在此期间,他不断看表,心中也越来越紧张。时间来不及了,他没法将张瑾玥安置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只能冒险越过连接南桥南路和北桥公园的小拱桥,爬上公园里的山坡避险。如果桥和公园都在的话。
想到这里,他懊丧不已,不由自主地发问,“我们通完电话后,你到哪里去了?”
“我想着你回来还要一段时间,就到裁缝铺给你改衣服了,想让你明天精精神神地把新工作照照了。那家店刚接了一批演出服,是急单,所以让我等一等。
我想呀,你找不到我就一定会去问于姐,再到铺子里接我,可是等到半夜也没等到你。铺子要关门,店老板说天要下雨给我一把伞,半路上真的下起来了。”
张瑾玥不急不徐地说着,声音在嘈杂的风雨中显得纤细无比。陈相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哪个字。
听完之后,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不忍责怪她,也没有道理去责怪。他想嘱咐她下次一定要好好呆在家里,却又觉得没有必要。
根据前两次的经验,一旦张瑾玥的死把他送回被电话铃吵醒的那一刻,除他以外的所有人,记忆都会重置。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一次也不会成功,因为他揽着张瑾玥的那只胳膊愈来愈吃力,两人的脚速也愈来愈慢。
这次也来不及了。
风雨越来越大,雨墙砸来,直接把陈相单手握着的伞砸脱。呜呜的风声震耳发聩,不时把树叶子、纸片和塑料袋刮到眼前。二人艰辛行走到拱桥,张瑾玥忽然跌倒了。
手上的重量一下变得很沉,沉到陈相用上两只手也没能把她扶起。张瑾玥顺势倚靠在桥头的立柱上,大口喘着气,半天才说出一句,“陈波,我肚子疼。”
张瑾玥颤抖的声音让陈相惊慌不已,他蹲在她身前,挡住不断砸来的雨墙,盯着她高高隆起的肚子不知所措。那里孕育着还未出生的自己。
桥下的水流声越来越大,哗哗声涌入他的耳朵之后似乎被困在其中,再也没有出来。张瑾玥的嘴一张一合地像在说着什么,但他的耳边只有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他从未这样无助过,眼睁睁看着她的裙摆逐渐浸在血水里,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当周遭的血腥味被如注的雨水冲淡,河堤下浑浊的水漫上脚踝时,张瑾玥的呼吸急促到像是下一秒就要中断,她捂住自己的胸口,剧烈咳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她的上身慢慢歪倒滑落在桥面,浸在泥泞的河水里。陈相伸手去扶,奋力托起她温热的后脑,把她揽在怀里。下一秒,沿河冲来的湍急水流把二人冲散。
水下,陈相再一次被血腥味包裹。吸入鼻腔的水是温暖的,但是后脑很疼,比儿时被玩伴失手推倒头磕在窗台上的那次还要疼。
2001年,陈相6岁。
“狗杂种。”
当眼前留锅盖头脑后拖着一根小麻花辫的同桌指着陈相鼻子骂出这句话时,陈相既气愤又疑惑。
他不明白这位和他朝夕相处的熊杰小朋友为何总对他充满敌意。也许是玩三打白骨精时自己总赢,也许是考试的时候没让对方抄卷子,又或者单纯是因为自己年纪小看起来好欺负?
可不论如何,骂人是不对的,于是他大声质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熊杰狠狠擦了一下鼻子,昂着头说:“你爸姓赵,你妈姓张,你姓陈。不是杂种是什么?垃圾桶里狗都不要的野孩子。”
陈相不明白熊杰的逻辑,于是追问,“你和你爸妈一个姓?”
“当然。我和我爸都姓熊,王琳的爸妈都姓王,张彬彬的妈妈也姓张,只有你,你跟你爸妈都不是一家人,不是杂种是什么?”熊杰的眉毛抬得高高的,肉嘟嘟的鼻子一抽一抽,让陈相想起动物园里向游客乞食的狗熊。
“你胡说!我是我妈生的,不论我姓什么都是我妈生的!你个胡言乱语的熊瞎子。”陈相不甘示弱。
“你再说一遍?”熊杰走近陈相,居高临下地冲他瞪眼。
陈相丝毫不怕,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你是熊瞎子。”
熊杰气呼呼地把脸憋得通红,狠狠推了陈相一把。陈相的头重重磕在一楼教室的窗台上,不远处法国枇杷墨绿色的树冠一下子模糊了。
那天剩余的两堂课,陈相都没有去上。他在医务室里不停哭泣,既为疼痛的伤口,也为错过的数学和科学课。他一直哭到放学,哭到班主任送走所有孩子后专门陪着他,因为张瑾玥没有来接他。
班主任联系了陈相家里的座机和赵栋梁的手机,但都无人接听,于是只好亲自把陈相送回家。
那时,陈相已经不哭了。他推开没锁的门,急匆匆地冲进屋里,寻找张瑾玥的身影。他想问她为什么自己不姓张也不姓赵,可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只发现了晕倒在厨房里的张瑾玥。
于是他又开始哭了。
赵栋梁始终联系不上,是王奶奶和于婶一起把张瑾玥送到医院的。陈相茫然地扒着病床,望着来来往往穿白色衣服的医生,于婶和他们交谈,说着陈相听不懂的话。
晚上,陈相坐在病房外冰凉的铁长椅上,不停地打哈欠,眼睛快要粘在一起时,赵栋梁终于脚步匆匆地赶来了。他忙碌好一阵后,才终于注意到孤独无助的陈相。
陈相见自己被注意到了,才噙着泪水小心翼翼地问:“我妈怎么了?”
“生病了,做个小手术就能好。”赵栋梁的脸拉得长长的,眼皮耷拉着。
陈相听张瑾玥能好,一下子开心了一点,但后脑隐隐的疼痛又把他拉回闷闷不乐中。
“你姓赵,我妈姓张,我姓陈。熊杰说我是狗杂种,是真的吗?”他说着泪水从眼角溢出来,十分委屈,“熊杰欺负我。”
赵栋梁的反应丝毫不像陈相期待的那样。他既没有回答陈相的疑问,也不关心熊杰做了什么,更没有要为自己的孩子讨公道的样子,而是把眉头皱出刀痕,一脸嫌弃地说:
“哭哭啼啼的,跟小姑娘一样。没出息。”
“叮铃铃铃铃……”
当眼前重归黑暗时,陈相的耳边传来熟悉的铃声。
他猛地坐起身,面前大红色的话机像一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