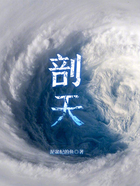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14章 风暴潮(七)
凌晨1点半,湛江市气象台灯火通明。那间挂有“防台指挥部”铭牌的办公室,也不例外。
平平无奇的办公桌上,并排摆着三部平平无奇的话机,银灰色磨砂塑料壳,面板按键,电子蜂鸣器,崭新的。
张援朝用脸和肩夹住话筒,手指在号码本上滑动,把一串号码读出声,边读边按电话键。电话拨出后,听筒里整整嘟了一分钟,无人接听。
于是他把歪疼了的脖子摆正,一手接住滑落的话筒,重重摔回到话机上。他刚刚打给水务局,但无人接听。
20分钟前,他收到任天富有台风靠近的报告,之后便立刻向省里汇报。得到指挥权后,马不停蹄地开展防台调度工作。
在过去的15分钟里,他给水务、交通、电力、通讯、消防等两只手数不清的部门去了电话,结果接通的不到三分之二。
作为一个在半夜喝浓茶提神的人,他本能地埋怨那些失联的单位,埋怨他们的值班室此时空空荡荡,连个能当传话筒的人都没有。
他想破口大骂,却又自觉理亏。确实,他通知得太晚了。以往的防台调度都是至少提前12小时安排。12个小时都不够,经常有单位埋怨他给的时间太少,林场接橡胶乳的碗还没回收完、市中心的广告牌还没加固好、港口还有船在进港、出海的渔民没全回来……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次的台风非同以往。它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上生成,本安安稳稳地走北东北的路子,谁知走了一半忽然调头。调头还调得特不是时候,刚好遇到卫星故障,两三个小时都拍不到它。它像一个饿死鬼一样飞奔到湛江,11点时还风平浪静,1点多风雨就大到要吃人。
狂风疯狂撞击门窗,墙体嗡嗡地震,好像真是被吞进了血盆大口里,马上要顺着拥挤的食道滑下去,滑到能腐蚀一切的胃里。
咣的一声,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又被迅速合起。开门的一下子,风把雨送进门,浇在张援朝脸上。
张援朝闭眼狠抹了一把脸,再睁眼时,看到任天富立在跟前,穿着墨绿色胶皮雨衣,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又加强了。确认是强台风,半小时变压17hPa,气压计和风速计都超量程了。”任天富说,任由兜帽内侧聚集的水流顺着脖颈流进领口。
张援朝捏着眉心,既愤怒又无奈,“都跟你说不要去观测了,我要指挥权也就用了5分钟,不差你这一组数据。这么大风,你不要命了?”
任天富似在忍痛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惊喜,“要到了?那赶快安排群众撤离吧。”
张援朝额头上的水珠刚被擦干净,就又冒出来了,“撤离?风都这么大了,人一出家门就给刮飞了,还怎么撤离?你知道台风在哪里登陆,12级风圈要扫过哪里?且不说撤离需要人力物力时间,我们连个路径预报都拿不出来,万一前脚刚给人转移到自以为的安全区,后脚台风就奔那里去了呢?”
张援朝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撒出来了,冲眼前这个兢兢业业一片赤诚但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里纸上谈兵四年,办事一点都不考虑后果,浑身上下冒着无知者无畏的傻气。
本以为这番针针见血的质询能给任天富好好上一课,可后者说出一句更让张援朝震惊的话:“只撤离沿海地势低的地方,让他们往内陆走走,或者找栋结实的楼上房顶,把风暴潮躲过去。”
任天富的这番话彻底把张援朝点燃了,“你们这些嘴上不长毛的,一天天脑子里想得都是什么?这么大风发生风暴潮的可能性确实大,可它具体什么时候发生?涨水多少?潮锋路径是什么样的?哪条路容易被波及哪条路不容易?你能答上来吗?没有这些信息,我拿什么调度?
你让居民撤人家就撤了?你们平常预报的那么烂,没给你扔臭鸡蛋就不错了,空口无凭让人大半夜冒雨出门人家凭什么听你的?”
张援朝刚说完,面前的三个话机接连响铃,他手忙脚乱一个一个接听,心脏发紧。海岸线附近的风力已经全线超过12级,上上下下各个系统都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不是他们以为的下一阵、刮一阵就能过去的,不断有居民致电询问是不是有台风来了。湛江港出事了,有船只在早已过饱和的港内走锚,撞成了一片。
更要命的是,他所埋怨的人现在开始埋怨起他。水利专家管他要台风路径、消防让他划出预计受灾区域、港口问他要不要鸣风暴潮预警的风螺,全是他给不了的东西。
张援朝在这行干了近30年,从预报员做到台长,做到防台指挥部的指挥员,全市的部门都要接受他的调度,什么大风大浪大灾都见过,游刃有余,问心无愧。而这一次,过往的职业高光被不知哪里蹦出来的台风全然击碎,自己也变得像刚入行担不起一点责任的新手,马上就要晚节不保。
此时的张援朝十分懊丧,心中充满悔意。他后悔没有在梁福歧提退休的时候强硬阻拦,逼他多带出几个预报好手再走;后悔为了分吃一锅饭的人尽量少,所以没向省里多要些人;后悔自己过于守旧,看不到数值模式的价值,没能让那帮时髦年轻人尽情捣鼓;后悔提拔陈波提拔得太早,让他变得恃才傲物,当班时间敢一声不吭就回家,只留下一群扶不起的阿斗和自己并肩作战。
接连响起的电话铃没让他感伤太久,听筒那头传来的消息没有一条是好的。
凌晨1点50分,南桥河畔。
一棵颇有些年岁的老榆树立在河边,枝叶杂乱。陈德球伏在它还算坚韧的树杈上,身下是愈来愈湍急的河水。
一个小时以前,他丢失了用来吃饭的四轮车,白捡回一个两轮的。偷车贼似乎知晓今夜的风雨非同一般,所以给他留下一辆锈到掉渣的二八大杠,好让他不用走着赶路。将近20里地,刮着风,走到中午也走不到地方。
这里离人民医院只有不到8里了。十几分钟前,他顺着荒草丛生的小道,一路摸黑北上,顺利来到这个靠近繁华市中心、烟火气十足的地方。柏油路比泥地好骑得多,目的地就在眼前,可他却被狂暴到顶不住的风雨困在了这里。
这场雨非同一般,不是傍晚时分下下晚上就能停的那种。风大到差点把他推进河里,雨点锋利得像刀子,从四面八方割来,让人受不住。这一定是靠海吃海的官渡人最怵的东西:台风。
陈德球出生在官渡村,那里位于河海交界处,微生物丰富、咸淡适宜,不用怎么操心,就能把蚝养得又肥又大。
陈德球祖上两代都是蚝农,每年夏天,他们把木板与竹竿交错捆绑制成浮排,一串串满肚卵的蚝被悬吊在浮排的竹竿上,孕育出密密麻麻的蚝苗。指甲盖大小的蚝苗在那里安然生长,到第二年的冬季就会长得比拳头还大。
冬天是官渡村最热闹的时节。蚝农们三五成群,将蚝排拉回岸边,拖出几十斤重的蚝串,撬出巴掌大的蚝肉,放入桶中,一片忙忙碌碌。有时候,还没忙完,买家就乘着小船慕名而来,把刚撬好的蚝肉成桶买走,挑都不挑。
傍晚时分,蚝农们会从船上拖下卖空的桶,倒扣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上面,迎着渐暗的霞光数票子,数到脸上笑开花。
但这样的好光景不是年年都能看到。白吃白喝老天爷的,自然就要忍受它时不时甩来的脸子。养育出雪白肥美的生蚝肉需要一年,但毁掉它们只要几个小时。
台风带来的持续大风大浪会把浮排破坏,蚝苗散落在海里,再也寻不着。海底的泥沙被风浪搅起,底层的冷水被带到海面上,水质水温剧烈变化,让蚝滤食受阻、应激而亡。
台风是蚝农们最害怕的东西,因为每当艰难熬过狂暴的台风夜,战战兢兢地跑到岸边查看浮排时,他们总会收获一片腥臭的海和退潮后散落在泥滩上的破碎蚝壳。
面对这样的心碎之景,家底厚的蚝农会叹叹气,安慰自己可以就此歇息一年。而家底薄的,只能抹掉泪,背上铺盖卷,到村外讨生活。
陈德球属于后一种情况,八年前的一天,他失去了所有浮排和蚝苗,被迫走出生他养他的村子,到陌生的城市里,去吃无尽的苦。
他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先是靠为木材厂搬货为生,后攒钱学车。他师傅说他开得最稳,把他推荐给湛江名头最大的储运车队,让他成为一名大货车司机。开大货可挣钱了,挣得比养蚝多得多。
于是他实实在在地过了几年好日子。娶媳妇,生儿子,盖房子,风光得要命。他儿子陈贵虾生得好看但十分胆小,一看见海就哭,经常被村民调侃以后没法养蚝。每到这时,他总会一把抱起贵虾,蹭贵虾肉嘟嘟的脸蛋,宠溺地说,“贵虾以后不用养蚝,你阿教你开货车。”
一想到贵虾,陈德球就好像被抽掉全身的力气,一个劲地往树下滑。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他攀树枝的手脚不知道该往哪里使劲。犹豫很久之后,他抽出缠在腰上的白膜的一头,在树枝上扎扎实实系了个结,一下子身子便又稳稳当当的,仿佛被胶水粘在树枝上。
借着昏昏的路灯,陈德球发现了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雨是越下越大的,可河里本自南向北急急流动的水,忽然之间放缓了,像被什么挡着似得,流动不开,打着旋往堤岸上面溢。河水上涨很快,一下子就漫上堤面。接着,周遭的灯全熄了。
无月之夜里的黑暗浓到化不开。陈德球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身下总是有水溅上来,这让他感到可惧,好像那诡怪的水马上就要淹到他。风一直吹在身上,但呜呜声似是小了许多,尤其是身后,一下子格外安静。他别过头去察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团团迷朦的灯光。
电依然没有恢复,不论是东边的小学校还是西边经常热闹一片的巷子,都还是漆黑一片。那些灯光很远,跳跃着,像是墓地里的鬼火。它们丝毫不避人,就那么从远处跳着压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有红的绿的和白的。
很快,陈德球便知道那些是什么了。那些灯光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像元宵节里的天灯,徐徐飘过来。有的一路通畅,有的被地上的建筑阻隔,一下子熄灭,每熄灭一盏,远处都会传来连绵的巨响。那些是船,漂在天空的船。它们歪斜着,漂得不高,有的从小平房上一越而过,有的与之相撞,碎裂之响震耳发聩,震得树枝都颤抖,
当陈德球能够借其中一盏的光亮看清桅杆凌厉的形状时,他感到自己垂落的脚浸在了水里。下一秒,整个人被吞没。
水下,陈德球拼命解自己刚系上的结,越用力,身体就越被白膜嘞得疼。解开后,他把白膜团成一团抱在怀里,蜷曲着身,在心中发出最后一丝残念:贵虾,尼阿今晚见不到你了。你要活,至少要比我活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