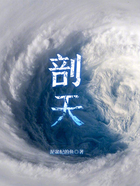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24章 命里有槽
“叮铃铃铃铃……”
铃声刺耳,冷气冻人,枕在额头下的胳膊麻木刺痛。陈相缓缓坐直身,木然注视话机上的灯光倒影,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浸泡在覃斗芒果中的那一夜,给他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也让无穷轮回的离场之路变得明晰。
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但善本身无法逆转任何东西。对人情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渴望奇迹的发生,那是专属于小孩子的奢望。不是所有人都愿做粉身碎骨的螺丝钉,更不可能因为一朝一夕的相处就把自己随意托付出去。覃斗芒果带来的厚重信任,是只局限于二横巷的美好童话。
所以,办法只剩下一个:用一份无可挑剔的预报产品,让张援朝相信自己所预测的一切。
现在是晚间10点半,他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完成这件事。在那之后,他要乘陈德球的顺风车赶回二横巷。张瑾玥只有亲眼见到他才能平安。
2个半小时,在一个观测资料匮乏的年代,基于十分有限的天气分析经验,能辅佐自己的只有一个古老而粗糙的数值模式。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别无选择。
“富哥?小任?天富!你快来看,南海上是不是不太平!”陈相站在值班室门口等待一会儿,成功等到脚步匆匆的任天富,迎着任天富表情复杂的脸,把他拉到电脑面前。
任天富迅速浏览了各个气压层上的天气图,将界面停在500hPa上,“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一条588线,很光滑,但它在南海上断掉一截,谁知道那里会不会有短波槽之类的东西,这地方要是能有槽,那咱们这里未来也不可能太平得了。”
任天富说完深深叹出一口气,把界面切到卫星图像窗口,那里一片空白,“说实话这图要是给我画我能画出10种不同的样子,海上的站点太稀疏了,想确认只能等卫星数据。”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9点半的卫星图像凑活能用,菲律宾以东有个气旋正在往北走,不来咱们这边。就算来也没事,咱头顶上也有高压,能把它给挤走。”任天富说着转头望向陈相,“波哥你什么意见?”
陈相断然是不可有什么意见的,任天富的分析无懈可击,就算罗城汉来估计也挑不出毛病。他本就没打算在这些花花绿绿的图上找突破口,所以迅速把话题转到模式上。
“天富,你帮我插值,用的什么方法,能教给我吗?”
任天富挠头答,“最简单的双线性插值,站点太稀疏的地方凭感觉估算,把有问题的数据点去掉,给你一个相对光滑的初始场,你好拿去跟卫星数据做同化。这还是你教我的,你有新想法了吗?”
得知插值过程需要人为干预后,陈相打消了把它写成程序节省时间的念头,转而热忱地望向任天富,“没有,你赶快帮我插,我这边调模式参数,咱俩配合起来早转完早预报早睡觉。”
任天富挠头的手依然没放下,顺从地往红木桌走去,期间不舍地回瞟陈相几眼。陈相一分钟都不敢耽搁,从抽屉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最末处,定下心来阅读。
这一次的目标更加清晰,但也更加有难度。他现在要做的不只是照本宣科把模式转出结果,而是依靠主观修正的观测场,和久远且有成片缺省值的卫星数据,让台风的风眼在屏幕上按照既定路线走到既定位置。
这就像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寻找一只特定的蝴蝶,然后捏着它的翅膀只让它展翅到特定弧度,如此这般,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才能行走得恰如其分。
计算机模拟的好处在于永远给人重新来过的机会。如果模拟结果不如意,可以调整初始场和参数后再次重复。这好比他可以试着捏很多只蝴蝶,也可以对蝴蝶翅膀多次尝试不同的弧度,直到龙卷风如愿刮起。
但困难在于当前的处境为他施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时间。即便调用全部核心,模式运转一轮也至少要20分钟,他只有6次机会。
这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绝望。即便他自己不被无数次的死亡实感击溃,即便用理智说服自己不必共情于张瑾玥分娩时的痛苦,他也不允许自己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无限次地试下去。
就算这是一场梦,真实世界中的时间也一定在流逝。在那里,名为查帕卡的恶魔更加凶猛,每晚一分钟,张瑾玥就多一分被闷在水里的可能。在真实时空中,他没有机会重新读档。
因此,从不信奉任何神明的他,第一次在心底对无名之神发出最为虔诚的祈祷,祈求几十分钟后,漆黑地图上的白色年轮,能在标有0701 01:00 BJT的图像里,出现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他的诚心似乎起效了。凌晨12点整,在失败3次之后,白色年轮终于在雷州半岛附近显现。但遗憾的是,登陆地点和降水量的预报结果,都与实际有出入,并且他无法在那些花花绿绿片子里找到一丝瑞云湖暴雨的线索。
结果不尽人意,但没有时间了,只能硬着头皮用。虽然这一次注定失败,但他已熟记数据和参数,只要能找到引导张援朝的方式,便可在下一次重新来过时,摆脱这荒谬的一切。
敲开张援朝的门,指出对天气图的质疑,献出模式结果。终于,在凌晨12点半,他如愿迎来一场紧急会商。
会商室十分狭小,几张方桌拼在一起,其上摆着一部电话。显色惨白的投影仪嗡嗡作响,几乎所有人都目色紧张地盯着幕布。门外,渐起的风在为他们捧场。
陈相顶着那些或迷茫或赞赏或审视的目光,硬着头皮讲完了他刚编的故事,基于主观调整的初始场数据、主观设置的模式参数和主观的期望。
在他的故事里,巴西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振翅理所应当地引发了惨绝人寰的龙卷风,但没人知道他自己就是捏蝴蝶的人。
从投影幕布旁走回自己的位置时,他听到了张援朝毫不掩饰的叹息。
张援朝把脸皱成沙皮狗,冲环坐在自己对面的5个人扫视,“大家没什么意见吗?”
没人应答他。张勇坐得端端正正,手下压着一本崭新的真皮笔记本,笔记本上别着一根橙红色笔杆、黑色笔顶笔尾、银色宽环的钢笔,这是整间屋子里最精致的东西。自始自终他都没看幕布和张援朝,而是频频瞥向身边的林芳。
林芳倒是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在短边翻页的横杠笔记本上记录。她很专注,专注到无暇打理越过耳后垂在脸颊边、略微遮挡视线的头发。任天富坐在她旁边,脸皱得比张援朝还紧,一只手放在自己肚子上揉。他坐得离林芳很远,像刻意躲避似的,两人之间的距离松垮到可以再坐一个人。
任天富身边,赵栋梁被挤得很局促。他缩紧身子靠在椅背上,目光放在身前那本厚厚的牛皮纸书上,面无表情,似在神游。
陈相坐在赵栋梁身边,一半身子转向右侧的张援朝,只留给赵栋梁半个后背。
“没什么意见我说说我的看法。”张援朝端起身前的茶杯喝下一大口,没有吐掉漂入口的茶叶,而是直接嚼嚼咽下肚,“陈波的整体思路是有说服力的,9502确实有登陆湛江的可能。但有一点我有异议,我不认为9502在登陆后能维持和加强,以至于引发强降雨和洪灾。
陆地上是个冷高压,9502要么水汽被切断,要么暖心被破坏,脆弱得很,根本蹦跶不了多久,更不可能引发陈波妄想的那些灾难。”
张援朝说完,神情复杂地瞥了一眼陈相,又扫视其他人一圈,“平时挺能说,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蔫了。都发表一下看法。”
张援朝从张勇开始,逆时针一个一个人盯过去,像点了一个无声的名。
“我觉得波哥说得对。”张勇不假思索,说完还冲陈相笑了一下。
“我还得再想想。”林芳还在对着幕布抄写。
任天富的目光在张援朝和陈相身上来回切换,犹豫半天才说:“从天气形势和模式结果来看,确实没有什么要素能支撑台风加强和特大暴雨。但波哥的模式是拿9点多的卫星数据转的,时效不是那么好。
我建议我们看看有没有新数据传过来,有的话让波哥再转一遍。”
任天富说完,捂紧肚子站起身,字正腔圆,“张台我想去趟厕所,然后再看一眼数据。”
目送任天富离开后,张援朝抬手捏上自己的眉心,余光里瞥见赵栋梁身前的那本《渔樵问对》,发出一声弱不可察的叹息。他没有询问赵栋梁的意见,而是转头看向一脸紧张的陈相。
“陈波。”张援朝把手放下,露出一张语重心长的脸,“你一直都是梁福歧的得意门生,但现在看来还是学艺不精了。我建议你把你的那什么模式先放放,让预报的重心回到天气分析上。也多带带天富,多教他分析天气图,而不是上来就让他学模式。
那种先进东西,让中央那帮专家折腾去就行了,高不高科技的,都不如吃饱饭重要。”
“好了,散会。陈波尽快按我刚提的思路整理一份预报结果,其他人在自己岗位上原地待命。”
在张援朝站起身之前,陈相拦住了他。陈相把投影仪投出的图像切到一张水汽场沿东经110度的经向剖面,指着北纬22度700hPa上的一个大值中心说,“张台,虽然当前的天气形势和模式结果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但你看这里,根据模式模拟,1点的时候这里的水汽骤然增大,还是有建立水汽通道的可能的。”
陈相死盯张援朝,大气都不敢喘。张援朝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反驳道:“1点是有,但12点半的时候有吗?1点半的时候有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凭空出来一团水汽,这难道不是一种虚假的扰动?
你到底是有多崇拜那团破铜烂铁,才能有失偏颇到这种程度?我还要去指挥防台,别再用你那套歪理谬论纠缠我了。”
陈相还想继续解释,但张援朝显然没有耐心听下去。他冲陈相摆摆手,把屁股彻底和椅子分离,端起茶杯就要走。当那只粘着碎眉毛的手快要触到门把手时,空寂的屋子里响起一句嗓音喑哑的嘟囔。这声音弱到几乎听不到,小心翼翼的,像是从没吃饱饭的蛤蟆嘴里发出。
“我支持陈波的观点,1点之后,大气中低层有建立水汽通道的条件。”
任天富的离开让空间松快很多,但赵栋梁依然缩身坐着,连手指都蜷缩起来了。
“你具体讲讲。”张援朝转过身,立在原地说。
赵栋梁没有动弹,只不冷不热地冲陈相耳语,示意陈相把图象切换到晚间11点接收的,700hPa的天气形势上。
“湛江北部、广西南部、北部湾附近,未来可能会有槽移过来。”赵栋梁说。他没有看图,也一直避开张援朝饶有兴致的脸和陈相惊喜到发光的眼睛。
“怎么得到的结论?这图上一点线索都没有吧。”张援朝立刻追问。
在众人的期待下,赵栋梁开始坐立不安。他嘴唇嚅动几下,却一直说不出来话。末了,当所有人的耐心都全然耗尽时,他终于有了动作。
赵栋梁终于舍得拆开大腿上那个蜷得很紧的拳头,把手抬到桌面上,捏着厚重《渔樵问对》的书页侧,把它立起来,让书脊上的大字书名冲着张援朝,然后吐出不可思议的几个字:“我算出来的。”
几秒钟的沉寂之后,张勇率先爆发出一声毫不掩饰的哂笑,紧接着林芳抬起扶笔记本的手,捂住自己的嘴。陈相眼中的光没了,张援朝把脸囔成一团,散发出怒气。
“我还以为你问天买卦这么多年,终于舍得回归人间了呢。”张援朝满脸愠色,“你的这个结论我可以帮你推导,很简单,就四个字:命里有槽。”
张援朝的怒火镇压住一切,连张勇都丝毫不敢动弹,不敢弯腰去捡掉在桌下的笔。赵栋梁和张援朝对视,眼神怯生生的,像是等待大人训话的孩子。
他没有等来。张援朝并没有再在赵栋梁身上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只干脆利落地转身,握住门把手,拉开门。张援朝的动作很大,以至于摔在墙上的门页把本就鼓鼓囊囊的墙皮磕掉了一块。
时钟指向12点40分,任天富还没有回来,张勇向陈相示了个眼色后也拉着林芳离开了。陈相立在原地,被失望和绝望包裹。渐起的风不断闯入室内,灌进《渔樵问对》的书页里,把皱巴巴但依然立挺的牛皮纸书皮吹得哗哗响。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那里未来要有槽的?”陈相问赵栋梁,语气诚恳,“现在没人在,就只是咱俩私下交流一下,你压力别那么大。”
赵栋梁侧脸对着陈相,连眨几下眼,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一下子站起身,一只手拍在被风掀起一半的书皮上,用十分硬气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我算出来的。”
赵栋梁离开后,会商室里只剩下陈相一人。他把先前展示过的图片重新放映了一遍,依然寻找不到任何线索。逐渐狂暴的风摩擦门缝和合叶,不断发出尖锐的哨音,却无法刺穿他的迷惘。
对陈波巨大的敌意,对张瑾玥可谓越界的在意和关怀,异常珍惜的《渔樵问对》……赵栋梁身上一定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像一粒微不可察的孢子,落在葡萄酒桶里,经过20余年的光阴,把本应醇香的甘露变得酸涩。
陈相向来不愿以恶意揣测别人,他十分希望赵栋梁不是那个到处扬孢子的曲霉菌落。可也许,对于赵栋梁的怪异行为,“命里有槽”是一个最为诗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