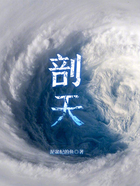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31章 决断
时间没变。
冷雨刺骨,周身剧痛,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让他回想起带血的裙摆,不住干呕。他的肉体十分痛苦,但心中在狂笑。
历尽千辛万苦,他回来了,回到2021年的雨夜,再一次面对蹑影藏形的台风。但万幸的是,时间没变。
02:01是26年前,萨利激起的风暴潮,席卷湛江沿岸的时间。但如今,查帕卡才将将靠近。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应对查帕卡超自然的轨迹,再一次挽回一切。
手机嗡嗡振动,来电显示为赵栋梁的号码。陈相果断挂断,给张瑾玥回拨过去一个。
电话被秒接,张瑾玥温婉的声音听得他想哭。他极力压制住自己翻涌的情绪,斩断三千思念和积压已久的疑问,只以格外冷静的口吻安排她和相熟的邻居一起前往华都汇避难。
两人对话间,赵栋梁呼入的电话一直闯入来电等待的队列,把陈相本就难以压抑的愤怒撩拨到马上破胸而出。那个薄情的老头,在得到灾难来临的一手消息后,不第一时间安顿好自己的瓷婚之妻子,而是将本能争分夺秒救人一命的电话打到本就安全的儿子这里。可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慈父,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领导。
陈相清楚,在来电等待的尽头,必然是焦急的质问或怒火中烧的骂言。质问他对台风路径的看法,骂他在火烧眉毛的时候不知溜号到哪里,一连十几分钟都找不到人。
因此陈相并没有理会赵栋梁,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值班室。他要争分夺秒先把模式运行上,这才是当务之急。
返回值班室的路上,山脚下不断传来各种刹车停车的声音,半山腰也人头攒动,不断有从山下开上山头的车把人接走。主楼门口,或相熟或生疏的人与陈相擦肩而过,都皱起眉头,不断回头看他,脸上挂起关切,脚下却不停。
艰难爬上五楼,整个楼层空空如也,打开值班室的门,迎接他的是一声惊呼和高梵被吓得煞白的脸。
几乎所有在岗的人都被叫到山脚下的预警中心帮忙了,轮休的也正在被召唤回来。由于灾情重大,省里接管了防台指挥,市气象台只留守高梵一人。而高梵的主要任务是见到陈相后,第一时间告知他也去预警中心。
很显然,查帕卡正在靠近的消息已像刚烧开的水一样沸腾。
但陈相不为所动。寒冷和疼痛包裹周身,头脑却格外开悟。他出生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风云雨电相处了26年,湛江市上的这一小方天空是他的老熟人。他谙熟它、研究它、剖析它、模拟它,他了解它身上的每一个脏器、每一条血管。
不论省里的、中央的超级计算机算力有多强大,经验有多丰富,都不如面前正在运行的、根据当地观测数据精心调整过参数化方案的模式来的精准。参数化是对各种非线性的、不闭合的方程组的简化描述,是除初始场之外影响模式模拟准确性的最关键因素。
所以,陈相依旧没有理会手机上无尽的来电,只按原计划把迟来的卫星数据同化进初始场,驱动模式试图得到水平空间分辨率百米级的台风生命周期。这是应对这场灾难的最短路径。
空调被调到电辅热,暖风吹在身上,让陈相脑后滴答下淌的血迹逐渐干涸。自那声听得人心颤的惊呼后,高梵没再发出一丝声音,只默默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在驱动和等待模式运行的20多分钟里,陈相丝毫没察觉到她的存在,只在注意力集中的间隙,从余光里看到摆在桌边的热水、毛巾、创可贴和纱布。它们安安分分呆在那里,不争不抢。
时间到,模式积分完最后一步。陈相一边满心镇定地查看结果,一边把手伸向毛巾和热水。虽然心中抵触,但赵栋梁他还是要见的,他要穿越冷雨,把眼前这份完美无瑕的预报产品送到预警中心。
然而,目光触及屏幕的下一秒,他手中的水杯跌落在地。
高梵很贴心,给的是四五十度的温水,没让他本就布满擦伤的身体再受一劫,但也没能温开他冷成一团的心。模式运行的十分顺利,结果却出乎意料。
查帕卡的17级风圈依旧出现在模拟视野中,但相对上一次模拟,位置偏出好远。上一次模拟中登陆点位于霞山区一带,而这一次,则显示查帕卡会略过东海岛、擦着徐闻县,直奔海南去。两次模拟仅间隔不过几十分钟,不应该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一瞬间,陈相再次慌张起来。集合模式的诡异预报结果开始悬在眼前,挥之不去。他原本以为,集合预报中的成员模式对查帕卡未来路径的预报之所以格外发散,是因为模式调试有误,是一个人为事故。而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其他可能,比如,查帕卡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
台风是天气尺度系统,属于大尺度运动,大到只在中低纬度出现而无法出现在赤道上,需要科氏力的存在才能生成。天气系统的尺度越大,描述它的核心方程组就越容易被简化,它的结构也就越清晰,不论是在人脑里还是在计算机里。
过去的几十年里,相对于龙卷、对流单体和湍流运动等小微尺度系统,人们对台风的研究是充分且透彻的。数值模式对台风的模拟即便不完全准确,也不可能拉跨到如此地步。
一顿自我内耗后,陈相选择不信邪。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东西凌驾于科学之上,于是把手头各种数据资料和参数设置相组合,设计出十几种不同的试验,降低模拟分辨率,让它们并行运行。他倒要看看,眼下的这个诡谲东西到底能离谱到何种程度。
用于模拟天气的程序,时间复杂度一定会在O(n^3)以上,每提高一点分辨率,就会引发难熬的漫长等待。但同样,如果反过来,每降低一点分辨率,都可以把漫长的等待凝为一瞬。
堪堪等待十几分钟后,运行结果成功输出。他迫不及待查看,差点又把刚端在手里的新的一杯水也丢到地上。
12个模拟试验的结果叠加在一张底图上,以不同颜色标注,它们从台风2小时前的历史位置上延伸出,各自发散,像是一把扇子。更离奇的是,扇子的骨架自扇钉处就开始发散,连查帕卡当前的位置都无法复现。
作为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将近10年的准专家,他的认知被彻底超越了。
凝神思忖之时,赵栋梁的电话又一次打进来。这次陈相没有再抵触,而是秒接,以一句“我现在就过去”打发掉对方,然后利索挂断。
用被冷落了许久的毛巾草草擦掉脸侧、脖子上和手臂上的血迹,陈相立刻出发了。既然决定打发赵栋梁,那就打发得彻底一点。超自然的现象自然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解决,如果连人类文明中最前沿的算法们都无法对台风路径达成一致,那么就让它们的创造者来做决定吧。
走出值班室时,陈相已做出决定。他要舍弃所有的算法辅助,以誓无二志的态度,直接给出结论:台风将在霞山区登陆,并引发风暴潮。
至于原因,他并不打算再像忽悠张援朝那样给出一个自认为完美但实则蹩脚的分析论断。他现在是首席,相当于一个科室里资历最高的主治医师,会诊的时候,他的意见有足够的分量。
客观和主观从来都是相对的,直感可能只是灵魂混乱的呓语,也可能是先于逻辑推理产生的对客观事实的快照。大气是混沌的,大脑也是。
在2点01分,意识和时间都被冻结的时刻,他曾在一个扭曲的时空里旅行10次之多,只为救下张瑾玥和霞山区的一切凡尘。台风在霞山区登陆就此成为他笃信无疑的直感。
他向来是一个理智的人,自学会1+1=2起,就从未相信过任何科学框架以外的事。这个夜晚,是他第一次放弃掉自己恪守的观念。但他别无选择。
被风推搡着走到山下的预警中心时,时间已指向凌晨3点半。那座明亮了整夜的单层玻幕墙建筑,已被水汽晕得模糊。陈相推门而入,穿过人头攒动的大厅,来到赵栋梁所在的小隔间。他倚在门口耐心等着,等待赵栋梁把手头的电话打完才去推门。
百叶窗叶片一致向下,投在双层夹丝玻璃的阴影挡住隔间里的一切映像,但陈相十分轻易地脑补出一张眉头皱得像刀痕的、无助焦虑的脸,像一只掉入蛇窝的癞蛤蟆。他马上就要把它解救掉了。
门开,赵栋梁和陈相对视,刚刚爬上脸的愠怒被惊讶取代,他嘴唇嚅动半天,才憋出一句和表情不相符的话。
“一个多小时不见人影,你是想造反吗?”赵栋梁问,眼神不断上下飘,打量陈相的全身。
“查帕卡会在霞山区登陆,叠加天文大潮,引发特大潮灾。你安排相关居民撤离,一切责任我担。”
陈相没有回答赵栋梁的问题,而是直切主题。他说得坦然自信,比面对张援朝时还要自信,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低姿态的祈求。
赵栋梁的眉拧得更厉害了,难以掩饰的费解逐渐挂上脸,“你转模式转出的结果?”
“不是,我就是单纯知道它要去霞山区。我说了,你按我说的做,一切责任我担。”陈相面无表情。
“这责任你担得起吗?”赵栋梁怒言,“你应该是清楚的,预报不力我只要挨几顿批评,最多台长的帽子不要了。但……”
“但倘若撤离过程中有一人伤亡,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陈相截住赵栋梁的话头,代替他说。
“可你还有别的办法吗?”陈相直视赵栋梁的脸,反问。后者嘴角开始抽搐。
“我说了责任我担。不论出任何意外,你都可以把责任往我这个首席上推。反正我要走了,你的风险我替你抗,你的帽子我帮你扶着,我够意思吧?”陈相云淡风轻地补充。
赵栋梁显然愤怒到极点,脸上微微抽搐的神经开始牵动眉毛。
“你这是越权!”他冲陈相吼,“不管你明天要去哪里,今天你都还是在岗的。岗位上,我是你领导,别用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跟我说话!”
赵栋梁显然气急了,但陈相毫不在意。关键时候,不争分夺秒处理业务,反而在人事问题上发泄情绪,这帮当台长的人似乎都喜欢做这种不专业的事。他早已司空见惯。
于是他继续淡然地把话题调转回来,像教小孩子识字一样,赐予赵栋梁不曾给过他的耐心,“模式全部失效,台风路径未知,天气分析毫无头绪。查帕卡在湛江登陆也好,不登陆也罢,广州湾的大风大浪都是免不了的。霞山区必然是最危险的地带,轻则湛江港撞成一片,重则沿海城镇一片汪洋。”
陈相立在赵栋梁的办公桌前,注视对方把早已泡黄的茶水喝干,又补充道:“我的看法并不完全主观,霞山区是有台风登陆和受灾历史的。26年前,我出生的那一天,有一个叫萨利的强台风就在霞山区登陆,造成了特大潮灾。你不会忘了吧?”
陈相不急不徐地把这段话吐完,赵栋梁刚好斟满新的一杯茶水送到嘴边,被实打实呛了一口。
他掩嘴咳嗽,眼神里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咳了几声后,又换上不容置疑的严肃模样,对陈相摆手,“这件事不再讨论了。你若是没能力做出正常点的预报,就找地方把你那烂脑袋缝一缝,然后收拾东西滚蛋!”
赵栋梁说完,狠啐一口茶叶,把脸囔成一团,又小声嘟囔出一句话,以最咄咄逼人的语气,“烂泥扶不上墙。”
一瞬间,忍耐已久的不满再也憋不住,像俯冲带上的火山口一样,爆裂式喷发。为赵栋梁为保乌纱帽而不管不顾几十万生灵,也为赵栋梁对自己的态度。
时间跨越26年,赵栋梁从卖卦哥一跃成为台长,却始终是一个草包。他没有批判自己的资格。
雨点打在落地玻璃窗上,格外嘈杂,仿佛重回经历过无数次的那个喧嚣雨夜。赵栋梁年轻时消瘦的脸和格外厚实的那本《渔樵问对》一齐悬在眼前,让陈相理智全无。此情此景下,他终于问出积压在心底已久的疑问,以嘲讽的语气。
“如果我说我给你的预报是用《渔樵问对》算卦算出来的,你是不是就信了?“陈相双手支撑桌面,向赵栋梁探身,“毕竟,你也经常这样做嘛。”
赵栋梁一脸讶异,半天没说出话来。两人长久对视,陈相的心跳得像打鼓。不论那离奇的十次轮回有多热血和感动,陈相都不希望它是真实发生的。尤其是最后的那次,拯救几万生命,让他如愿回到现实,却又把他的心戳得千疮百孔。
他的心愿落空了。在无尽的雨声中,赵栋梁脸上复杂的神情慢慢褪去,像幼虫期的蜚蠊,把皮褪去一层又一层,露出极度丑陋的身躯。
赵栋梁慌张且费解地问,“是谁和你讲起的?”
一瞬间,陈相开始失神卸力,像被浸泡在浓到化不开的水汽里,憋闷且绝望。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欺骗所有人?95年6月的最后一天,如果你有机会率先发现天气图的错误,是不是也要继续隐瞒你的能力,用一句‘你算出来的’来戏弄所有人?朝夕相处的同事,霞山区的几万居民,难道他们也都是你的仇人吗?”
陈相伏在桌子上,像被什么牵引一样,身体前倾,离赵栋梁的脸很近。一直以来,他都活在张瑾玥给他描绘的美好童话里,在那里,他有一个不完美但依然爱他的父亲,那个名义上的慈父,就像主旋律故事里的那样,因为心系大家而舍弃小家。
这是普世观念,他虽有厌恶但也不得不认同。这是他苟存在赵栋梁身上的唯一信念,是维系这不以血缘为基础的父子关系的唯一纽带。而现在,两人之间本就脆弱的连结被彻底击碎了。
他第一次如此仔细地观察眼前这张令人厌恶的脸。油光满面皮肤黯淡,眼袋叠在永恒的黑眼圈上,被岁月的沟壑填满。先前那股不许任何人忤逆的威严已从这张脸上全然褪去,只剩下惊慌与脆弱。
两人就这样僵持许久,谁也没说话。陈相清楚,时间是一条单行道,历史的轨迹只能有一条。第八次轮回中的“命里有槽”即便再真实,也已被第十次的情节所覆盖。他对赵栋梁的提问基于不可能发生的虚假假设,赵栋梁根本没法回答他。
但人心和人性都是可以不随时过境迁而改变的永恒存在。有些事情即便没发生,也能够跨越时间成为无可反驳的事实。他已从眼前这张怯懦的脸上读到答案。
有句话说,细细探索事情的真相,就会发现,你为之难过的,只是幻觉,它跟事情本身没有关系。可这句治愈的格言并没有在陈相身上应验。他的这位父亲,这位在美好童话里抚育他长大的父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
支撑桌面的手臂开始颤抖,陈相心底对赵栋梁留有的最后一丝余念被击穿了,他需要时间去面对,去消化。但眼下,查帕卡正在带来注定刻骨铭心的灾难,性命攸关,刻不容缓。他没时间脆弱。
于是他主动熄灭炙烤赵栋梁的那簇火,让话题重新回到眼下最紧急的事务上来。
“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对查帕卡的预测,才能干预到省里的决定,让生活在霞山区沿海10公里内低洼地的居民全都撤离?”
陈相收回带有压迫感的姿态,后退两步,定立在原地,重回冷静。
赵栋梁长叹一口气,整个人松弛下来,捏着眉心说,“给我一份无懈可击的预报产品。只要你能拿产品说服我,我就能为你的观点作背书,去向上传达。”
赵栋梁说完,犹豫一阵后又补充一句,“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权利很局限。我只能为你提交台风路径,剩下的事,包括风暴潮增水路径、撤离范围、时间地点等等,都有一整套成熟的决策流程,我干预不了。
你能做的,我能为你做的,我们能为湛江市居民做的,都只有一件事:把台风路径预报准。”
返回值班室的路上,雨在持续。风一阵疾遽,一阵缓滞,金边红桑残叶纷飞,茁壮的棕榈树上,刚萌发的新叶不断裂响,像被掰断的水萝卜和刚入口的冰草。
一切都是那样熟悉,连空气里的泥土气息都与26年前的那个雨夜别无二致。再一次的,陈相有机会带着时光之河下游的风景逆流而上,却仍旧无法获悉究竟要搬动哪一块山石,才能让芸芸万物都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一条远离死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