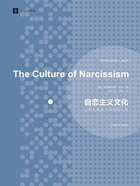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精神治疗的情感
我们当今的气氛是治疗性的而非宗教性的。今天人们渴望的不是各人灵魂得到拯救,更不用说让早先的黄金时代得到重现,而是一种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心理安宁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片刻的幻觉。即便是60年代的激进主义,其作用也不是一种替代性的宗教而是某种形式的精神治疗;许多人置身其中,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原因。激进政治充实了许多本来十分空虚的生活,给生活带来了一定的目的和意义。苏珊·斯特恩在回忆“气象员”派的吸引力时所用的语言与其说使人想起宗教倒不如说更使人想起心理分析与医学。她试图回忆自己在1968年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参加示威时的心情,结果却大书特书起自己的身体状态。“我自我感觉良好,可以感到自己肢体柔软、结实又苗条,跑几英里根本没问题。我的腿走起路来坚定而敏捷。”数页之后,她说:“我有了一种真实感。”然后她又多次重复道,和重要人物在一起使自己也感到不平凡起来。“我觉得自己是一大群热切、激动而卓越的人中的一部分。”当那些被她理想化了的领袖人物就像通常情况下那样使她失望时,她又寻找新的英雄来取而代之,并希望通过他们的“英明卓越”使自己重新变得热情起来,从而克服她自己的无足轻重感。和他们在一起,她有时觉得“坚强、稳定”——但当她发现那些被她崇敬的人“傲慢无礼”,“对他们周围的人都不屑一顾”时,他们身上迷人的光环又消失了。她又孤零零地被排除在外了。
斯特恩回忆录中的许多细节应该为那些早年具有革命心理的学生们所熟悉: 包括她对革命事业的狂热,小组成员们对政治教条的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党派中每个成员都被劝说参加的、试图使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符合革命信仰的那种无情的“自我批评”。然而任何革命运动都无不带着那个时期的文化的一些特点,而这场革命所包含的成分立即就表明它是美国社会前景暗淡时期的产物。“气象员”派所生活的环境——一个充满了暴力、危险、毒品、性放纵、道德和精神混乱的环境——与其说是来源于更早一个时期的革命传统,不如说来自当今美国的动乱和自恋主义苦恼。苏珊·斯特恩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精神及健康状况,以及她依靠他人才能感觉得到自我存在,这些都使她有别于那些在政治中寻找一种入世的救世方法的宗教追求者们。她需要的是树立自我,而不是让自我淹没在一个更大的事业中。从其关心自我这一细微特点来看,自恋主义者也不同于被R·W·B·刘易斯、昆丁·安德生、麦克·罗金和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些19世纪观察家们分析为“美国的亚当”的早先一类美国个人主义者。当代的自恋主义者与如此频繁地为19世纪美国文学所讴歌的“强悍的自我”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们也以自我为中心,也追求空想中的辉煌。美国的亚当与他们今天的后代们一样,试图使自己跟过去一刀两断,建立起爱默生所谓的“与宇宙的新关系”。19世纪的作家和演说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杰斐逊的信条,即地球属于活着的人。与欧洲的决裂,长子继承权的废除,以及家庭关系的松散给他们的信仰提供了切实可能性(尽管末了这也只是一场虚幻),好像全世界所有人中唯有美国人能够从盘根错节的过去的影响下逃脱出来。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人想象“他们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说,美国的社会状况使以前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连在一起的那条纽带被一刀斩断。“时间之纬已被切成碎段,而代代相连的那条轨道也被彻底抹去。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很快就被遗忘,而对于将要到来的人,人们毫无概念。人的兴趣完全局限于那些在时空上跟他关系最近的人。”
一些批评家也用类似的语言叙述了70年代的自恋主义。彼得·马林认为,由人类潜力运动激发的新治疗法教导人们说,“个人意志是强有力的,人的命运完全由它决定”。因此他们强化“个人的孤立”。这一观点属于那个体系完整的美国传统社会思想范畴。马林提请人们注意“人类社会巨大的中间地带”的呼吁,与范·威克·布鲁克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布鲁克斯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无视“人类传统中那宜人的中间地带”持批评意见。布鲁克斯在形成他自己对美国文化的批判时,也曾从桑塔亚那、亨利·詹姆斯、俄瑞斯特斯·布朗逊(Orestes Brownson)和托克维尔这样一些早期批评家那里得到灵感。(8)他们所确立的那种批判传统至今还可以对肆意膨胀的个人主义的恶劣性作出有益的批评,但我们有必要把19世纪的亚当主义与我们时代的自恋主义的不同点考虑进去,对原批评加以修改。对“独处主义”的批判尽管有助于保持人们对社会的需要,但随着真正的个人独立的可能性的消失,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当代的美国人也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建立不了任何一种共同生活,但是与此同时,现代工业社会的聚合力量又已经瓦解了他们的“独立性”。现代人既已向公司献出了他掌握的绝大多数技能,就再也满足不了他自己的物质需要了。家庭不但丧失了其生产功能,并且也丧失了它的许多再生产功能,以致男男女女们在没有领有一定文凭的专家的帮助下甚至都抚养不了孩子。自助传统的衰退也使一个又一个日常生活的功能消失,并使个人依赖于国家、公司和其他官僚机构。
自恋主义是这种依赖性在人类心理上的反映。尽管自恋主义者不时会幻想自己权力无限,但是他却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尊。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他那种脱离家庭纽带和社会机构束缚的表面自由并不能使他傲然挺立,也不能使他作为一个个人发出光辉。相反,这种自由带来了他的不安全感,只有当他看到自己那“辉煌的自我”形象反映在观众全神贯注的眼神里时,或者只有当他依附于那些出类拔萃、声名显赫、具有领袖才华的人物时,他才能克服这种不安全感。对自恋主义者来说,世界是一面镜子,而强悍的个人主义者则把世界看作是一片可以按他的意志随意塑造的空旷的荒野。
在19世纪美国人的想象中,向西延伸的连绵不断的大陆既象征着摆脱历史所带来的希望,又象征着它带来的威胁。西部向人们提供了建立一个不受封建禁锢束缚的新世界的机会,但是它也诱使人们抛弃文明并回到野蛮状态。通过强制性的工业化和无情的性压抑,19世纪的美国人以微弱优势战胜了他们的本我。他们向印第安人和大自然发动的凶狠的攻势并非出自不加约束的冲动,而是出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超我意识。他们畏惧西部的蛮荒状态,因为它是每个人内心蛮荒状态的物化。尽管他们的通俗文学将边疆肆意浪漫,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在这片荒野上建立了一种一面克制冲动,另一面又放任对财富的渴望的新秩序。资本积累以其本身的特点抬高了贪欲的地位,而使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属于为后代的服务。在力图赢得西部的鏖战中,美国的先驱者们的贪欲和残忍达到了极点,但他们总是把未来想象成一个和平、高尚、虔诚、妇女儿童受到保护的社会。这种向往通过一种对失去了的天真的怀旧狂热地表现出来,而且其中也带着某种疑虑。他设想他的后代会在道德高尚的女性“文化”的气氛中成长,一定会成长为头脑清醒、遵纪守法、驯服的美国公民。想到后代会因此有那么多的好处,就使他的辛苦劳动变得有意义,同时也使他认为他的残暴、肆虐和强奸行为变得情有可原了。
今天使美国人绝望的不是这个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的世界,而是他们针对这个世界而树立起来的那个陈腐无能的社会秩序。原先为了把各种可能性局限在文明范围内而设置的社会约束已深入他们内心,这使他们内心充满了毁灭性的厌倦感,就像被俘虏了的动物的本能会退化一样。重归野蛮状态的威胁对他们的震动是如此之小,致使他们干脆渴望起一种更强有力的、随本能行事的生活。今天,人们常常抱怨失去了感受的能力。他们力图培养更生动的体验,想把慵懒的肉体鞭笞得再度充满生机,并指望衰退的欲望重新复苏。他们谴责超我,颂扬已逝去的感性生活。20世纪的人们对强烈的情感树起了如此之多的心理屏障,并在这些防御中投入了从他们的本能中汲取来的如此巨大的精力,以至于人们再也记不得充满欲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往往容易陷入因受到压抑的欲望所引起的狂怒之中,而为了克制狂怒,他们又设置起新的防御。他们表面上和气、驯服而又合群,但内心翻腾着的愤怒却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官僚社会很少能找到合法途径使其得到发泄的。
官僚机构的发展产生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它注重为人处世的技巧,而使美国亚当们那放浪不羁的唯我主义无立足之地。可与此同时,它又侵蚀了各种形式的家长制作风,因而削弱了原先由父亲、教师和牧师代表的社会超我意识。然而机构化的权威在一个表面宽容的社会里的退化,并没有导致个人内心“超我意识的退化”。相反,在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禁律消失了的情况下,它促使了一种严厉的、惩罚性的超我意识的发展,这种超我意识从本我意识中最具破坏与侵略性的冲动中汲取了大量的精神能量。超我意识中的无意识的、不合理性的因素出来控制了超我的活动。随着现代社会的权威人士失去其“可信性”,人们的超我意识越来越多地起源于孩提时代对父母的原始幻想——充满虐待狂的幻想——而不是起源于内化了的、儿童长大时接触到受人爱戴的社会行为规范后才形成的个人理想。(9)
我们这个社会在要求人们服从社会交往的原则的同时,又拒绝把这种原则制定成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保持心理平衡的努力促成了一种与具有强大自我的人们那种初始的自恋主义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自我专注。古老的因素越来越主宰人们的性格结构。按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说法:“自我缩回到一种被动而原始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世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形式。”自大狂式的、急于经历各种体验的、傲慢的自我退化成了表面堂皇、自怜自爱、婴儿般的空虚的自我。如鲁道夫·乌利泽(Rudolph Wurlitzer)在《木垛》中说的,它成了“一个黝黑而潮湿的洞,各种东西迟早都会在那儿找到栖身之地。我呆在洞口处,搬运着胡乱塞进来的物品,边听边点着头,慢慢地我也融化于洞中了”。
因深受焦虑、沮丧、莫名的不满和内心空虚的困扰,20世纪的心理人既无意追寻个人的自我扩张,也无意求得心灵升华。他只想找到心理安宁,而今天的情形却越来越使这一愿望也变成泡影。在他为心理安宁而进行的斗争中,他的主要同盟不是牧师,不是提倡自助的流行吹鼓手,也不是工业巨头型的成功典型,而是治疗学家。他向他们求助,以期获得“心理健康”——即相当于当年的灵魂拯救。精神治疗成功地继承了强悍的个人主义与宗教的地盘,然而“精神治疗的凯旋”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意味着它已成为一种新宗教。精神治疗是一种反宗教。它之所以如此确定无疑并不因为像精神治疗医生所鼓吹的那样,是由于它坚持理性的解释或科学的治疗手段,而是因为现代社会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而它对除目前需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一概不感兴趣。即便当治疗学家谈到人对“意义”和“爱情”的需要时,也只是把它们简单地说成是病人情感需求的满足。他们几乎从来不曾想到——只要考虑到心理治疗这一职责的本质,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要他们想到——鼓励人们让自己的需要和兴趣服从于其他人的需要和兴趣,服从于超出自己利益的事业或传统。自我牺牲或自我贬低意义上的“爱”和服从一种更高尚的忠诚所具有的“意义”——这些崇高的感情对治疗学家敏感的神经来说是压抑而不可忍受的,是违背常识并有害于个人身心健康的。把人性从这些过时了的爱和职责观念中解放出来,成了后期弗洛伊德治疗学,特别是它的皈依者和鼓吹家们的使命。对他们来说,心理健康意味着打破一切禁忌,并让个人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