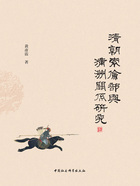
二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范式
中国民族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又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方向。2010年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专业中国民族史方向攻读博士时,即关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术传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老一辈史学家王锺翰先生的清史满族史研究国际知名,陈连开先生的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国内知名,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王锺翰先生将清史与满族史结合起来,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选择。从清史转入满族史、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始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这从《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中可见端倪。该日记从1954年记至1957年,可从日常的研究生活中窥见王锺翰先生的学术实践。如撰写《满族在未统治中国以前的社会形态》《努尔哈齐兴起之际的社会性质问题》《皇太极时代的满族社会性质问题》《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呼尔哈部不是达呼尔人》《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明代女真人考略》等,这些论文有的与最后发表的题目略有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出王锺翰先生满族史研究谋篇布局之思路。其特点是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史研究,同时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考据之功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先行者,与民国时期的研究范式迥然不同。
陈连开先生于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之后,负责中苏边界谈判资料整理,此时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开始了研究中国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其间通过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机会,得到郭沫若先生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北方防御,南方浸润”的指教。陈连开先生认为这一观点从宏观上概括中国民族关系史不是很准确,但的确有重要启发。[5]我亦认为郭老的宏观阐述难以涵盖中国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但是北方注重军事防御,南方注重文化浸润,确实说出了中国南北民族关系史的差异,对研究微观区域民族关系史有重要指导意义。邸永君先生的经典之作《民族学名家十人谈》(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陈连开先生访谈录》对陈先生的学术史贡献有详细的访谈整理,在此不赘述,但其中提到陈先生之观点“中国各民族交替作用,共同缔造了统一中国,并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争取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总的趋势”[6]。该观点对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继而从史实上辅佐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几十年后回顾和理解了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
近年来李大龙先生从族群凝聚与融合的角度探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历程实际上也是王朝对区域内区群不断整合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7]在对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学术争论进行学理评析后,指出时代呼唤中国民族史学界“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8]。晚年的费孝通认识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学理价值,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是对顾颉刚观点的完善。[9]并对中国主体族群的凝聚与融合做出纵向的梳理,提出:“古代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独特的以文化特征为显著特点的划分族群的理论体系,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众多政权也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对境内的族群进行着整合。”[10]族群整合在古代和近代中国没有条件去完成,这是新时代留给当今中国人的历史重任之一。
与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针锋相对的是内亚史研究。19世纪80年代俄国学者莫希凯托夫提出“内亚”的地理概念,到1940年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英文版出版,内亚史研究在欧美史学界十分繁盛。“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11]内亚史强调地域色彩和宏观视角,中国民族关系史注重立足实际与考据相结合,这两种研究范式本可相互补充,但是由于史观立场的差异,近年来双方争吵不断,集中于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上。在内亚与中原的关系上,姚大力提出:“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问题上前后相继、一脉相续的历史线索。这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12]汪荣祖先生认为:“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内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内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13]那么,新清史倡导的东北—内亚主轴重于传统中国的江南—北方基线,大清帝国的满洲因素重于中华帝国的儒家思想[14],遭到了中国大多数清史学者的反对,其高潮是李治亭先生《“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B02版)一文的发表。李治亭批驳新清史学派的清帝国主义论、清朝非中国论和满洲外来论,维护大一统的原则立场。姚大力提出“从东到西”的过程在最近的一千年里所取得的显著成果,真正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15]。结果立即被汪荣祖驳斥:“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16]清朝的中心在东不在西,首都在北京不在承德,中央在中原不在内亚,统治在中华帝国的儒家思想而不在满洲特性八旗制度。
对于新清史提出的清朝是个殖民帝国,在大一统语境下实难成立,姚大力极力为殖民主义的概念辩解,将殖民主义的概念普世化,认为“殖民化是通过人口的集体移居而创建殖民地的活动或过程。殖民化的历史内容是一个世界由以被发现、被开发和被人居住的庞大进程。殖民化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的历史”[17]。这种观点将人类的一切历史都归为殖民化,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随后他将中国境内的人口迁徙说成是未产生殖民地的殖民化过程,并提出一国当中“内殖民主义”的概念。试问未产生殖民地怎能被试为殖民化过程!将一国之内的统一问题称为“内殖民”,有别于外殖民,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字游戏。葛兆光支持姚大力,认为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至少有三点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第一,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第二,是为了掠夺资源,还是纳入帝国;第三,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还是要逐渐把蛮夷与华夏同质化。”[18]汪荣祖与姚大力针锋相对,认为“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是两码事”[19],当属公正之论。俄罗斯帝国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以夺取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开拓市场为目的进行侵略[20],而清朝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其战略是保守的,噶尔丹破坏了喀尔喀蒙古的生活秩序,威胁到北京的安全,圣祖才御驾亲征。高宗经略新疆没有经济掠夺的动机,却为了祖国统一而损失钱财,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诉求。“西方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几乎全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图?多的是劳民伤财,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清既然是为了北疆的安宁与安全,可称为‘义’。”[21]清朝只是占领了新疆,没有占领阿富汗、浩罕汗国、巴达克山等中亚有意归附的国家,没有侵略外国的意图。钟焓批驳新清史构建的殖民征服叙事模式,提出清朝人口双向流动(汉人流向东北,满洲人流向关内)与殖民帝国人口单向流动(人口从殖民母国流向殖民地)截然不同。[22]
新清史强调全球化视角,回应新清史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由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交往史观、全球史观组成,与前三种史观相比,严格说来全球史观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史观。“全球史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跨国的联系、交流与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3]全球史观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批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后,各国需要在史观上摆脱“欧洲中心论”,超越民族国家或地区的阻隔,摆脱孤立的历史研究。全球史观并不能与唯物史观在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抗衡,然后所倡导的精神却并不是相互抵触。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的第一原则。”[24]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看待世界,用整体观认识问题,整体并不是简单的部分之总和。“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统一整体,整体性是系统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处理和解决系统问题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25]
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也很突出。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左”的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影响,使得人们过分关注于矛盾的斗争性,而忽略了矛盾的统一性。而矛盾双方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二者不可分割,对立统一。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典型的以论代史、脱离考据研究范式的集中反映,其中不乏学术贡献和史料梳理,但是围绕着“欧洲中心论”而展开的讨论,中国处在被动和从属的一方,在中外比较的过程中,过多地关注于差异,而对中外的交往交流研究得很不够。
全球史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多应用在世界史研究,而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这固然有这一方法来自西方的缘故,也有国内长期将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割进行教学研究,如今在行政上归属于两个一级学科分别发展的行政导向有关。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意义重大,任重而道远。全球史观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也须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研治中国史,要避免“中国中心观”。同人类学一样,史学研究也要正确对待异民族研究和本民族研究的差别,在区域研究中跳出地区的藩篱和学科的壁垒,这样才能在中国发现历史。
新清史的清帝国主义论,其侵略扩张、殖民掠夺的史观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质是没有搞清楚中国的疆域范围,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必须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否则将无从谈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6]对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白寿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说”、孙祚民的“汉族王朝疆域说”,谭其骧的“18世纪50年代到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结果是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的认可,并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具有创新观点的是李大龙提出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到1840年的清朝疆域说”[27],理由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是清朝以“中国”身份首次在国际上签约,彰显了中国的政治属性。
2013年我进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时,又关注到吉林大学老一辈史学家张博泉先生提出的“中华一体”理论框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尤其是北方民族关系史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张博泉先生从学术史上拨乱反正,对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论”进行驳斥。指出“征服王朝论”的理论来源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南北民族对立论”,将渤海国、辽、金、元、清北方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相对立,将区域发展差异解释为游牧农耕“二元性”,人为制造帝制王朝与征服王朝的对立。“骑马民族论”对骑马民族分类混乱,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随意分类,将匈奴、突厥、蒙古称为纯粹的骑马民族,将女真、满洲这种畜牧、农耕、游猎并存的民族称为渐进的骑马民族,甚至将日本这一岛国也称为骑马民族,理由竟是“日本能吸收外国的东西,是开放性的社会”[28]。“征服王朝论”“骑马民族论”实为美国分裂中国民族和日本侵华的民族理论工具,他们想把北方民族划分出中国,违背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张博泉先生长期研究北方民族史和东北地方史,“中华一体” 理论是在中国地方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辅以社会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北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更有指导意义。
从宏观上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著作首推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29],该书摒弃了学术界烦琐的理论之争,摆脱了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分歧,对中国民族关系史做了提纲挈领的通史模式研究,具有奠基意义。
从微观上对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地区民族关系展开研究的专著当推吕光天、古清尧编著的《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30],该书把从古至今活跃在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民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做了梳理,重点对清代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研究,对其在边疆开发、与中原地区民族互动、共同组成多民族国家方面给予肯定。
以黑龙江地区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有周喜峰教授的《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31],该书是目前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各个民族及其社会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明朝末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到清乾隆末期二百年间黑龙江地区的满族、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回族、费雅喀族、库页族等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抗击沙俄入侵及军事驻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亦对清朝政府统一与治理黑龙江民族的历史过程以及各民族的迁徙和相互关系加以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的历史。作者根据正史与实录等相关史料,考证出黑龙江民族与满洲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敢于纠正旧说。康熙年间科尔沁蒙古所“献出”锡伯族中的达斡尔人来源问题,是一个已成定论的问题,《达斡尔族简史》等认为这部分达斡尔人是科尔沁蒙古于天聪八年(1634)俘获的。作者考证出这部分达斡尔人是崇德五年(1640)五月在清朝政府平定索伦部博穆博果尔叛乱后,由黑龙江上游迁徙到嫩江下游的索伦部达斡尔人,澄清了这一方面的史实。这部分达斡尔人同锡伯族等被编入八旗后,由于他们原在科尔沁蒙古属下时任官者少且官职低,因此其牛录的佐领均由锡伯人担任。他们同锡伯族一起驻防齐齐哈尔城,并承担坐卡巡边、保护台站、维护治安等任务。其附丁及家属则承担垦荒种田、交纳官粮、供养披甲等任务。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始,这部分达斡尔人又同锡伯族等一起,南迁盛京等地驻防,其后又迁往新疆,逐渐融入锡伯族之中。作者提出清兵入关对黑龙江地区的开发和少数民族的发展弊大于利,清朝政府的行政管理措施和民族政策非常成功,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对保卫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落后的地区有益于保持民族特色,这些观点很有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