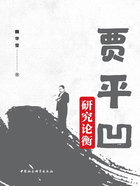
第一节 贾平凹的写作前史
追溯贾平凹的写作史,最早源于在水库工地的宣传海报。1970年,参军受挫的贾平凹来到丹凤县的苗沟水库工地,因字、文采俱佳,被安排编写《工地战报》,他一人身兼数职,既是记者又是编辑,同时要负责美工、刻字、校对、印刷等。在水库工地上,可以发挥贾平凹的特长,弥补劳动力较弱的问题。1971年11月6日深夜,他给远在唐古拉山当兵的同学的信中写道:“值得告诉你的一件事是:水库架设了一座长达600多米的空中索道,创造了商洛专区的第一个奇迹。”[1]但眼看着同龄人去当兵、去招工,贾平凹内心也曾无限迷惘,他写了一首诗,充满对自己前途的焦虑。
月亮升起了,
发着柔和的银光;
山风吹动了我的衣裳,
我掏出笔写下了我的衷肠。
四山这么荒凉,
银河遥远苍茫;
水库修好了我到哪里去?
丹江无语默默流淌……
因贾平凹在水库工地的优异表现,1972年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贾平凹的人生出现新的转机。多年以后,他在《我和刘高兴》中写道,如果不是升入大学,他的人生遭际大概和刘高兴差不多,甚至还会不如刘高兴[2]。入学时,系里要求每人写一篇上大学的感想,他写了一首长诗《相片》,从家乡棣花镇一直写到西北大学的校门,诗作在校刊上发表。该期的校刊,多是老师们的文章,学生的作品仅仅刊载贾平凹一人,也说明这一时期贾平凹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文采修养。之后,贾平凹一直勤奋写作,那时候,学校的墙报、笔报、校报、专栏等,凡是登文章的地方,到处有他的诗。“紧不行,慢不行,他又作了许多诗,有他多年的积郁,有他生活的琴音。”[3]
1973年,贾平凹与同学冯有源合作发表《一双袜子》,刊载于《群众艺术》第8期(内部发行)。此后,《群众艺术》发表了贾平凹的多篇作品,编辑费秉勋是贾平凹最初的赏识者和重要的研究者,从最初发表贾平凹的习作,到1980年开始系统研究贾平凹的作品并指导他写作,费秉勋一直呵护青年作家贾平凹的文学成长。仅费秉勋一人当时就发表相关研究文章30余篇,并最早撰写贾平凹研究专著《贾平凹论》[4](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可以说,费秉勋是贾平凹早期写作的发现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后来贾平凹曾写作散文《先生费秉勋》,追忆二人的相知和交往,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感激。
大学期间,贾平凹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文学作品,被实习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正在编“百花丛刊”的邢良俊收入《荷花塘》《小电工》,又在邢的建议下将《南瓜的故事》投稿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朝霞》上。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办学习班,帮助一些有创作基础的业余作者来出版社改稿,就邀请贾平凹参加:“一来请他帮我加工一些比较麻烦的稿子,二来可以使他享受到每天几毛的伙食补贴。”[5]这一时期,贾平凹正式开始文学创作。1974年10月,他创作的散文《深深的脚印》发表于《西安日报》,因之前的写作,都是发表在内部刊物上,这篇散文也被认为是贾平凹正式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12月,小说《荷花塘》和《小电工》被收入“百花文艺丛刊”的创刊号《荷花塘》。《荷花塘》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定印迹,写一个“红小兵”保松保卫荷花塘,和落后势力做斗争,不允许摘荷叶的故事。但也显示出贾平凹的文学特色:文字清新、优美,在主流的叙事中注重呈现自然风光之美。如保松首次看到荷花塘的感受:“这荷花塘呀,好大!一眼望不到头,只见一塘碧水,粼光闪闪,塘边垂柳把长发似的枝条一直拖进水面;一队队小船似的鸭子从枝条下轻轻划过去,钻进荷叶里。知趣的青蛙,从一个荷叶上跳到又一个荷叶上,溅得水珠在荷叶上骨碌碌地打转儿。哎呀,那荷叶开得多好看,红艳艳、鼓嘟嘟的,像小妹妹的脸蛋……”《小电工》同样是写“红小兵”小海和破坏发电站的“坏分子”王宝来做斗争的故事。在结尾,“月亮多明哟!明得就像用雪擦过的玉盘。溜溜南风迎风拂来,轻轻地抚摸着人的脸;白杨却鼓掌了:哗!哗!哗!把人心都拍醉了。啊,山寨的夜晚多美呀!月光下,清风里,小海和奶奶、王伯伯押着王宝来两口,威威武武向队部走去”。
1975年,他的诗作《回秦岭》被收录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诗集《山花红似火》中。这首署名工农兵学员贾干凹的长诗如下:离开秦岭三年整,秦岭常在我心中,大学毕业今又回,只见秦岭更年青——松柏翠,杜鹃红,水库深,麦田青,进村看梧桐,枝杆好峥嵘,树下小茅屋,门牌:医疗棚。双手抱住梧桐树哟,满怀激情往外涌——当年打游击,父亲战斗在秦岭。火线去包扎,战地去护送,医疗所扎在梧桐下,红旗挂在梧桐顶。破石窑里常常走,穷人叫他“红医生”,那年敌围剿,血雨浇秦岭,要搜伤病员,枪逼老百姓,为掩护群众出虎口,他血洒村头染梧桐……六年前,歌声中,我来插队到秦岭,梧桐树下开大会,唢呐吹打鞭炮鸣。支书赠宝书,贫农送药笼,从此扎根在山村,阳关大道朝前行!当年旧棚址,茅屋又重撑,一面大红旗,又飘梧桐顶。白天药箱“十”字红,夜里巡诊马灯明,攀崖藤,悬半空,草药一笼汗一笼……上了大学进北京,秦岭装心中,月月把信通:问东家,问西邻,问丰收,问卫生,再问梧桐下开过多少会?茅屋里为多少贫下中农医好病?今日回秦岭,风吹桐叶响,霞染茅屋红。满怀激情问一声:还认识三年前的赤脚医生?忽然村口人声喊,贫下中农把我迎。大娘把我拉怀中,开口却喊父亲名,说是“红军医”又回来了:一样的容貌一样的声,只是更年轻!说罢面向东方望,再叙贫农心中情:“山村有医生,咱把瘟神送,多少梦里笑出声,醒来仰望北斗星,如今大学生,又回咱秦岭。毛主席啊毛主席,时刻关怀咱山里人……”一人说罢百人和,百人唱起万山应——文化革命春雷动,新生事物多无穷,看杜鹃,杜鹃红,看梧桐,梧桐青,看罢大地看长空,万里神州展新容。回秦岭,情满胸,满胸豪情诉秦岭: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革命,巡诊不怕路途远,巡诊不嫌药箱重,要学雄鹰穿云行,顶风冒雨傲苍穹。一辈子战斗在秦岭上,革命青春火样红。回秦岭,秦岭迎,还挎红药箱,步伐更坚定,还拜老贫农,永当小学生。“六·二六”红灯当头照,为采中药攀山峰——豪情满怀看未来啊,继续革命脚不停[6]!这篇叙事长诗尽管带有“革命”年代的叙事与激情,但也可发现贾平凹对于秦岭的感情,后来他写出关于秦岭的多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山本》、散文《秦岭的美》等。
毕业后,因有25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邢良俊的帮助下,贾平凹很幸运地得以摆脱原籍,来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此时的贾平凹,“在编辑室里,他年龄最小,又是男同志,经常被支来支去出杂差,支援三夏,人防工程,唐山大地震时的救灾活动等等,五年编辑生涯倒有近一半时间驻外勤”[7]。一方面他要承担编辑的职责,写审阅稿件的退稿信;另一方面自己也经受着大量稿件被退回来的苦恼。他宿舍里有只白木箱,里边装着大半箱从全国各地退回来的稿子。这段编辑部的故事,在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中也有描述。因贾平凹总是利用各种琐碎时间写作,总体上被认为虽不是一位好编辑(痴心创作),但是一位好作家的前史[8]。
关于贾平凹早期的阅读史,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仅从散见的回忆或朋友的叙述中发现其最早的文学阅读。据冯有源记述,小时候的贾平凹爱读书,“为了读书,小小年纪一个上午给人家磨三升苞谷,借了三本书;为了读书,悄悄拿走了县城姨家没读完的《红楼梦》”[9]。“他的中学母校有个小图书室,红卫兵那阵,书也被偷光了,他打听到一些下落,常常就用帮工去换读。不仅是因为空虚,而缘于他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朦胧的爱。”[10]曾经有一段时间,贾平凹苦练毛笔字;同时,也开始读古书,包括唐诗宋词,甚至手抄《古文观止》等书。其间也读了鲁迅作品,《秋夜》的第一句就让他“眼里噙满了泪水”。后来,郜元宝在《贾平凹年谱》中写道,阴阳先生、狼虫虎豹,神神鬼鬼的民间智慧,以及那间“四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庙”改做的小学教室,浸染着商洛“雄秦秀楚”文化交界地带所特有的历史遗韵和自然风物,对于年轻时的贾平凹写作影响很大[11]。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因当时的特殊情况,图书馆中的国内外文学名著都被查封,连《创业史》也被封存,贾平凹只好去图书馆二楼的过期期刊阅览室进行文学阅读。此外,他最喜欢的地方,是西安市南院门的古旧书店。“那时,社会上好多人挨了批斗,吃了苦头,害了怕,视书籍为祸水,把书卖到古旧书店。而求知若渴的我们又从古旧书店买回来,便宜得很!好不高兴呢”[12]!这在当时集体贫困的年代,对于这些出身乡村的穷学生来说,能够买到便宜的好书阅读,简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大学读书期间,贾平凹曾因肝病被隔离一段时间,这样使得他有了一块小小的空间,并决定“要在此好好读一些书。开始书目杂一些,后来便捋顺了,先博后精,先泛后细,这是他的读书宗旨。他读梁启超,读王国维,读胡适之,皆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他们都是中国近代了不得的学问家”[13]。贾平凹这一时期读书庞杂,包括泰戈尔、鲁迅、孙犁、川端康成等。只要是能够找到的,都拿来读,尤其是孙犁的写作,对当时的他影响很大,后来还读到了沈从文的作品,受益良多。
1976年,贾平凹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作品集《兵娃》。全书收录了包括《荷花塘》《小会计》《小电工》《兵娃》《参观之前》《深山出凤凰》等儿童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一本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短篇小说集”[14]。这些作品的语言优美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展现出新一代农村少年在阶级斗争中茁壮成长的故事,同时展现出时代的新风貌。
贾平凹最早的研究者费秉勋指出,在大学期间,贾平凹就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在当时的作品中,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而是依靠艺术感知,描写农村、农民的故事,尽管主题相对概念,但是贾平凹对乡间景物的审美表达还显示出一位作家的审美能力与美学风格。而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之后,他的创作视野、题材也随之扩大。他开始关注乡村生活中的普通人,尤其是他们为了集体事业劳作的精神,在平凡中显示出的动人力量。从1977年开始,贾平凹开始找寻到自己的写作方式,《果林里》《第一堂课》将小说主角设定为青年男女,尤其是年轻少女。后有学者指出这和贾平凹此时的甜蜜恋爱人生经历有关[15]。而作品中对于青年男女的爱情与事业的描写,使贾平凹这一时期创作中田园爱情牧歌式的基调更为明显。后作品被结集为《山地笔记》[16]出版。在这些美好青年形象中,更多是倾注了贾平凹本人的人生观以及看待世界的温暖眼光,“通过描述青年男女事业追求中的纯真爱情,来抒写作家自我的感情经验”[17]。
梳理贾平凹的写作前史和阅读史,我们会发现作家的成长之路及文学阅读对于写作的影响。作为工农兵学员,贾平凹最初主要是靠阅读积累进行创作,难免带有革命时代风气,当他开始有自觉写作意识时,所抒写的多是自己的采风经历、观察与身边事。与费秉勋、冯有源等师友的交往互动也使贾平凹从儿童文学写作者更多转向古典文学阅读,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