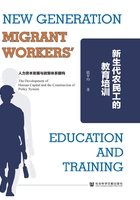
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各项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社会结构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李强,1996,2004;甘满堂,2001;接栋正,2013)。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三元社会结构中的一元。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我国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制造业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的40多年,见证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奇迹。他们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功不可没。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制造业中约70%的劳动力、建筑业中约80%的劳动力、第三产业中50%以上的劳动力均为农民工(金维刚、石秀印,2016)。虽然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等的影响,农民工没有充分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市民化、权益保护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中央政府开启了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进程,经历了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管理限制”、“积极引导”和“全面推进”(金维刚、石秀印,2016)等阶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学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进入21世纪,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社会融入等社会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和探讨的热点。然而,时至今日,农民工的“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境况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对处于“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和市民化是他们未来的出路,更是各级政府、全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往,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落实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破除就业歧视,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促进他们就业,但是对农民工教育福利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注略显不足。事实上,不管是实现就地城镇化或市民化,还是在输入地实现城镇化或市民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目前遭遇的主要困境已经从权利不平等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不足和教育福利缺失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低下和人力资本缺失,既影响他们自身在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化进程,同时业已或即将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与提升综合国力的掣肘因素。本书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和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建构”作为主题加以分析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且新生代农民工规模日益庞大,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增长0.6%,达到28836万人,比2017年(28652万人)增加184万人,约2.9亿人,超过总人口(14.0亿人[1])的1/5。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2017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9)。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的1/10还多(10.7%)。2008年底,国家统计局建立农民工统计监测的调查制度;2009年,首次公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止到2018年底,农民工总量从2008年的22542万人[2]增加到2018年的28836万人,增长了6294万人,增长率为27.9%。其中,2009年到2017年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5.4%、4.4%、3.9%、2.4%、1.9%、1.3%、1.5%、1.7%。尽管农民工数量每年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农民工总体数量在不断上升。这一点从图1-1可以看出。从2010年开始,农民工数量的增长率从5.4%一度回落到2015年的1.3%,2016年农民工增速又开始出现反弹,增长到1.5%,增长率比2015年提高0.2个百分点。2017年农民工数量增长1.7%,增长率比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8)。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日益庞大。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从2013年开始以年均0.8个百分点增加,从2013年占农民工总体的46.6%增长到2018年的51.5%。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相较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更具特殊性、复杂性和紧迫性[3]。

图1-1 2009~2017年农民工数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至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整理。
(2)新生代农民工“常住化”趋势明显,已成为制造业劳动力主体
随着政府出台越来越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甚至是突破性进展。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受严峻的就业形势影响,加上年龄大、体力衰弱和农村政策向好等因素的影响,老生代农民工逐渐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发展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并且已经成为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体(王志华、董存田,2012)。和老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追求的是在城市长远发展,他们更倾向于全家人一起外出,事实上他们更多地选择举家搬迁到城市居住、务工经商与生活。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常住化、家庭化”(钟涨宝、陶琴,2010)的“事实移民”。但是,他们“半城市化”(王春光,2010)、城市“边缘人”(郑杭生、洪大用,1994)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除了原有的一些政策体制性障碍以外,受教育程度偏低和人力资本严重不足也是阻碍他们在城市发展和实现实质性城市融入[4]的重要因素。
(3)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足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存在张力
与老生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状况难以满足未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足与产业结构不适应的矛盾在多年前蔓延的“用工荒”问题中已经暴露无遗。“‘民工荒’说到底,本质上是个伪问题”(陆学艺,2005),并非农民工数量的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童星等,2006)。这种“民工荒”“技工荒”等“用工荒”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表现,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难以改变的根源之一是其欠缺文化资本(钱民辉等,2011)。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主体。积极探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对于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促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已有的研究和农民工政策更多关注平等就业权的落实和其他权益的保护,就业培训实践存在过于侧重就业技能培训的局限
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关注农民工就业、政策体制性障碍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就业技能的提升,对于如何从人力资本角度摆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掣肘的研究略显单薄。尽管中央在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十二五”规划也曾明确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党中央也在2010年一号文件中专门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缺乏一部统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已有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和各地培训实践,多是应付上级任务的单一“就业技能导向型”培训,忽视了政策对象的“培训需求”,农民工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农民工培训“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地方投入资源虽多,但由于部门分割、多头管理,出现了资源的分散与浪费,以及培训的“碎片化”现象,培训效果不佳,而且大量农民工并没有得到自身所需要的培训。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培训政策名号响、效果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出台政策的部门投入的培训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是培训市场混乱,培训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培训资源垄断,具体执行培训任务的机构与管理部门存在某种利益瓜葛,社会培训机构参与不足,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培训既脱离市场需求,也不符合农民工需要。尤其是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因不了解流入地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流于完成培训任务的形式,甚至演变成套取国家培训资金的行为。流入地政府要么对农民工培训毫无兴趣,要么只为辖区内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不愿意为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而投入,担心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变成“为他人作嫁衣”的不划算买卖(金维刚、石秀印,2016)。如何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根本有效途径,也是唯一途径。人力资本不足和缺失的状况最终会影响到“农民工市民化”(郑杭生,2005)。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足的状况已经或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转型、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的巨大瓶颈。
(5)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研究很单薄,未成为国内研究的主流
一方面,相比对农民工的研究而言,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还不够,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为篇名和主题分别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截止到2018年9月5日,以“农民工”为篇名搜到的期刊论文有37715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4776篇),而以“农民工教育”为篇名搜索到的期刊论文只有309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9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819%;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为篇名搜索到的期刊论文只有67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8篇),仅仅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178%;如果以核心期刊论文计算,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为篇名搜索到的核心期刊论文只有32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8篇),仅仅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085%。剔除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话,篇名含“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核心期刊论文成果仅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064%。以“农民工”为主题搜索到的期刊论文有64630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8776篇),而以“农民工教育”为主题搜索到的期刊论文只有1126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431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1.742%;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为主题搜索到的期刊论文只有832篇(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431篇),仅仅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1.287%;如果以核心期刊论文计算,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为主题搜索到的核心期刊论文只有597篇(含431篇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仅仅占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总数的0.924%,不到1%,剔除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后,仅占0.257%。如果把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相关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成果计算在内,篇名含“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论文有41篇(含6篇硕士学位论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109%;19篇核心期刊论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050%。以“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为主题搜索到相关论文491篇(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87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760%;109篇核心期刊论文只占“农民工”研究论文总数的0.169%。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未成为国内研究的主流。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一是围绕市民化、城市迁移、城镇落户意愿与永久迁移意愿的研究(蔡禾、王进,2007;郭维家、蒋晓平、雷洪,2008;王兴周、张文宏,2008;张翼,2011;李强,2013;陆益龙,2014;张翼、汪建华、吕鹏,2014;熊景维、钟涨宝,2014;陆益龙,2014;毛丹,2015;潘泽泉、邹大宽,2016;李飞、钟涨宝,2017);二是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和城市融入的分析和探讨(关信平、刘建娥,2009;王春光,2010;王春光,2011;江立华、谷良玉,2013;潘泽泉、林婷婷,2015;潘泽泉,2008;孙立平,2007;彭华民、唐慧慧,2012;张文宏、周思伽,2013);三是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就业、经济收入水平、住房等)、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公共政策、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包括人际交往、人际适应、社会资本、社会参与等)、文化心理因素(包括教育、文化价值观、社会认同等)等方面展开(陆林,2007;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梁波、王海英,2010;孟颖颖、邓大松,2011;潘泽泉,2011;陈靖,2013;韩俊强,2013;秦立建、王震,2014;杨春江、李雯、逯野,2014;殷俊、李晓鹤,2014;汪华、孙中伟,2015;肖云、邓睿,2015);四是有关就业、收入、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强、唐壮,2002;王春光,2003;唐钧,2004;陈成文、王修晓,2004;李培林、李炜,2007;王春光,2009;李培林、李炜,2010;李培林、田丰,2011;张昱、杨彩云,2011;张翼、周小刚,2013;田北海等,2013;程诚、边燕杰,2014);五是从阶层、阶层分化、社会不平等与集体抗争等方面展开的农民工研究(王春光,2004;汪建华、孟泉,2013;黄斌欢,2014);六是关于农民工权利意识、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郑杭生、洪大用,1995;陆学艺,2003;李迎生、刘艳霞,2006;徐小霞、钟涨宝,2006;江立华,2006;关信平,2008;田北海、徐燕,2011;史柏年,2013;李迎生、袁小平,2013;秦阿琳、徐永祥,2014)。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陈成文、曾永强,2009;唐钧,2010;赵蔚蔚、刘轶俊,2011;雷万鹏,2013;孙彬,2014)、农民工管理(刘世定等,1995)与农民工“污名化”等问题(文军、田珺,2017)。
教育是民生的根基。“教育是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所系。”(郑功成,2004)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受教育水准,都既从根本上决定着每个公民的发展机会,又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曾指出,我国最大的民生是就业。我们要坚持积极就业政策,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以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要为民众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以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习近平,2017)。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劳动者必须具备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和素质。教育和培训是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重要渠道,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是关键。但是,从目前的研究以及政策实施来看,我们对教育,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极其有限甚至非常欠缺的。
改革开放40多年,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进入新时期与新发展阶段以后,我们的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党的十八大适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未来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不再以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源能源驱动,加快实现从低成本优势到创新优势的转换,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转型,全面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质增效。为此,2015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了我国要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强化基础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五大工程,要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技术含量高的十大先进制造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使我国进入制造强国的行列,为我国到2045年成为引领全球的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在于我们有高度发达的教育和培训,在于我们要切实高度重视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在于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培育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实现产品研发和核心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完全自主。此外,新兴的、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对工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大量能满足先进制造业需要的技能型高素质蓝领工人。为此,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建设,推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要健全对学生的资助制度和政策体系,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更多地接受高等教育(习近平,2017)。要完善职业教育培训政策体系,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要注重解决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习近平,2017)。
在中央号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际,全国各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的历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成为未来企业发展的趋势。作为农民工主体和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虽然比老生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是,目前他们的人力资本状况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岗位需求。如果不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切实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那么符合企业升级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的1/10还多,他们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群体的主体,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教育福利的缺失状况,不但会影响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与综合国力的提升,还会直接妨碍我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瓶颈。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综合能力和城市适应能力,是确保他们增能和实现在城市顺利发展的关键。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选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和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建构”作为主题,通过调查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状况、问题及成因,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由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组织、家庭与个人构成的责任共担、多元协同共治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打造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市场营利组织为补充、社区为依托、民间非营利组织为辅助、社工等专业机构为服务主力的多元参与、相互补充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服务网络,助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化进程,并为新兴制造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