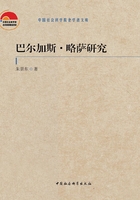
《绿房子》(1966)
《绿房子》是拉丁美洲新小说中的一部佼佼之作。作品问世后一版再版,多次获奖,被公认为最优秀的西班牙语小说之一。
《绿房子》全书包括四个章节和一个尾声。作品以皮乌拉省城和原始丛林为背景,交替、穿插描述了五个真实的故事。它们是:外乡人堂安塞尔莫在皮乌拉开设“绿房子”妓院、后被加西亚神父付之一炬和琼加重建“绿房子”的情景,贫民区四个外号叫“不可征服的人”的地痞流氓不务正业、败坏社会风尚的作为,来自丛林的印第安姑娘博尼法西娅的不幸遭遇和利图马军曹的种种经历,印第安部落酋长胡穆反对剥削的行动和遭受的苦刑,投机商人富西亚和阿基利诺的违法活动及领航员涅维斯的漂泊生涯。小说通过这些主要故事情节的描述,勾画出一幅当代秘鲁社会的缩影,再现了秘鲁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寻衅闹事、吃喝嫖赌的地痞流氓,有沦为妓女、惨遭蹂躏的土著姑娘,有心肠毒辣、面孔伪善的修养院长,有明火执仗的强盗和横行不法的军警,有深受压迫、受人宰割的印第安居民……作品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把原始丛林中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悲惨生活公诸于世。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白人冒险家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无情的欺压,使读者深深地感到,散居在马拉尼翁地区的阿瓜鲁纳人和乌安比萨人的生活与现代化城市的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当死气沉沉的现代化城市堕落到依靠妓院带来的夜生活来活跃气氛时,丛林深处的印第安人却“生活在史前社会的野蛮世界,那里毫无文明可言,其野蛮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反动统治的魔爪伸向了秘鲁的每一块土地,无论皮乌拉那样的喧闹城市,圣玛丽亚·德·涅瓦那样僻静的森林小镇,还是远处深山密林、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哪怕是一座孤岛,无一能够逃脱残暴的反动统治的魔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发现秘鲁是一个比我在来昂西奥·普拉多所了解的更为广大、更为可怕、更为恐怖的东西。”
从类型上讲,《绿房子》属于现实主义,它继承和发扬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美洲内地的原始丛林和热带大草原的严酷自然环境,统治者和剥削者支配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阶级矛盾,种族歧视,普通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凌辱、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自发的反抗斗争,是拉丁美洲的基本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中心内容。这样的内容在“大地小说”作品,特别是《旋涡》、《堂娜芭芭拉》和《堂塞贡多·松布拉》中得到了最集中、最令人信服的表现。这些作品通过对橡胶采集工人的悲惨生活,雇工的艰苦劳动,他们受到的残酷剥削,一般人民的朴素信仰,加乌乔的侠义精神,卡西卡主义,强悍而凶狠的女性,被原始丛林、草原和河流吞没的男人等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特点。巴尔加斯·略萨继承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被公认为一位笔触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位这样的作家,他十分清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作家必须全面地反映现实”,“应该像兀鹰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给以揭露和抨击,以加速旧世界的崩溃”。对秘鲁的社会状况,对秘鲁现存的社会制度,他十分了解。他深知,秘鲁社会是一个充斥着种种弊端,陈规陋习,种族压迫,等级森严的社会。他觉得那个腐败的社会就像一条恶狼,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分别代表政权、教权和军权,不断从腐烂的内脏里喷出毒焰,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熏倒、吞噬。巴尔加斯·略萨正是执着他那“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的笔,写出了《绿房子》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绿房子》的现实主义是和上述三部小说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绿房子》是它们的综合和统一。《绿房子》一开卷就把一幅酷似《堂娜芭芭拉》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样火热炙人的烈日,同样划行在浑浊河水里的木船,船夫说着同样的话语,旅客们同样忍受着窒闷的天气……在后来的描写中,虽然两者所涉及的地理环境、人物和问题不尽相同,文学风格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所表现的人与大自然的斗争、强者的肆虐、弱者的受欺是相同的,梦幻的气氛也是相同的,尽管其间相隔四十年之久、生产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绿房子》中的主要人物富西亚也像堂塞贡多·松布拉一样是个影子,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只是他的活动背景不是草原,而是河流、平原和丛林,他的职业不是赶牲口,而是做橡胶和皮革的投机生意。《绿房子》中的丛林也是一个漩涡,那里的居民也像《旋涡》中的橡胶采集工一样悲惨。这部小说不同于上述三部作品的新标志或新象征是“绿房子”。“绿房子”是建立在城郊荒凉的沙漠区的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去处,那里有的是酒吧、赌场、舞池,乌烟瘴气的气氛,地痞流氓的活动,麻木的市民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但是和上述三部小说相比,《绿房子》更为雄心勃勃,情节和结构更为复杂,文笔更为精细,思想内容也更接近土地、街头、城区、居民、山地和丛林。被迫离乡背井的丛林姑娘博尼法西娅就曾经说:“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的乡土感到耻辱的。”作者十分热爱他笔下的人物,怀着深切的同情对待他们,热情地描述他们的生活和反抗斗争。读者可以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成长中的国家的音乐,从他们身上看到美洲的一切敌人留下的伤痕,还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看到美洲的风沙、瓢泼大雨、熊熊的烈火、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特别是作为作品“主角”的圣地亚哥河。那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河流,是一条美洲的大河,它悠长、缓慢、不可驯服,仿佛一条巨蛇,无情而执拗地运送着私货、旅客,熏染着世界,危害着社会。拉丁美洲一向被视为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世界,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的武器除了火与剑之外,还有宗教、金钱和西方生活方式。但是只要那个“野蛮”的世界和不驯服的大自然不低头,外来的一切手段都将归于失败。美洲人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不过为了一个目的: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他们希望有一块面包可以充饥,有一点安宁可以享受。但是他们的敌人是无情的,是强大的。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持枪的警察,惑人的教会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地主。广大的土地和他们的命运被几只无形的巨手所掌握,统治手段极其残酷,任何不满和反抗都要遭到讯问、鞭笞、监禁和流放。甚至一个手势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从根本上讲,对美洲的“野蛮”社会和粗犷原始的大自然来说,欧洲的“文明”是无济于事的。殖民活动只能加深人民特别是土著居民的苦难,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弊病。实际上,这种文明带给美洲的东西就只有危害社会的弊端(如“绿房子”妓院),富西亚那样的野心勃勃的活动和试图改变印第安人的习惯、借以“拯救”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从《绿房子》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倾向看,它不失为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绘了世界,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抨击了不合理的世道,深刻体现了作者关于“文学是一团火”,是“对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武器”的创作思想。
在写作手法上,《绿房子》打破传统小说的俗套,大胆吸收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技巧,创造了具有拉丁美洲特点的新风格。例如在叙述故事时,把本来的时间、地点、独白、写景等的顺序打乱,故事的开始、发展和结局不拘泥于习惯的框框,在描述中既有跳跃,也有颠倒,既有独立,也有混合,既有并行,也有交叉,故事中套着故事,对话中夹着对话。这种异乎寻常的构思和叙述的方法,被批评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巴尔加斯·略萨则把这种手法具体概括为三种方法,即“中国的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中国的套盒术”即像中国的套盒术那样,“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中还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即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放在一个大的故事中,从而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所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运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从而产生催化作用”。这种手法的确能够收到引人入胜,使人惊讶的效果。但是这种手法可能使读者视为畏途,觉得像走入迷宫,困惑不解。因此,在阅读之前,必须对这种方法有所了解,阅读时小心谨慎,注意人称变化、情节或故事的转换。做到这一点,就不致感到困惑,产生莫名其妙之感了。
《绿房子》在描写人物方面也有一些特点。如果把整个小说比作一条河流,那人物的活动就像河面上起伏的波浪,他们随着河水的奔流,忽明忽暗,时隐时现。仿佛在银幕上一般,有的逗留时间较长,有的较短,有的一闪而过,有的甚至只在人物的访谈中存在。而且,所涉及的人物繁多,不像一般小说有几个主角,人物的外部特征也不明显(没有着笔描写人物的外貌)。这样做,容易给读者留下模糊的印象。但是,在《绿房子》中,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意图并非要塑造多么典型的人物(当然他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及其行为来反映社会生活和各阶层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使读者对社会现实获得深刻的、难忘的印象。一般来说,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绿房子》却迥然不同。这部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几乎都是真人真事。作者曾于1958年到马拉尼翁地区的阿瓜鲁纳人部落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小说中的镇长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就很像当时号称“黑金之王”的胡利奥·阿拉纳,他有一支军队和一个独立王国,本世纪初盘踞在马拉尼翁、亚马逊、纳波和普图马约等一带地区。作者曾经讲,他认识阿瓜鲁纳部落的酋长胡穆和日本投机商人富西亚。略萨对皮乌拉省城十分熟悉,特别是它的郊区曼加切里亚。皮乌拉的妓院是历史事实,小说中所写的就是他的耳闻目睹。作者还访问过森林小镇圣玛丽亚·德·涅瓦,在那里亲眼看到了修女们借助警察的力量捕捉印第安女孩,对她们进行所谓开化教育的情形。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博尼法西娅就是被修女们从丛林里捉来的一位印第安族姑娘。在作品中,她起着勾连原始丛林、圣玛丽亚·德·涅瓦小镇的修道院和皮乌拉省城三个重要活动地点的作用。博尼法西娅是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她被捉入修道院后,让她负责看管孤女,她出于同情,把孩子们放走了。修道院长审问她时,她表现得既固执、天真而又勇敢,是个质朴而纯洁的姑娘;被逐出修道院后,在拉莉塔撮合下她同军曹利图马结了婚,这时的她变得多情而温存,但是已经经不起异性的引诱,当军曹因决斗伤人被投入监狱后,她就轻易地被利图马的把兄弟阿塞菲诺所俘虏,等到她被迫沦为“绿房子”的妓女,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甘心被人凌辱和损害的女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的牺牲品的形象。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她的身世和遭遇,通过她对那个戕害无数善良平民的吃人世道发出强烈抗议。阿瓜鲁纳部落的酋长胡穆(作品暗示他是博尼法西娅的父亲),是丛林土著居民的灵魂,他性情执拗、坚强,富于反抗精神。为了对付白人的剥削,他准备成立合作社,把橡胶运到城里去卖,但是奸商们立刻勾结反动当局,派军队中途拦劫了他们的橡胶和毛皮,胡穆被抓走,当众对他施以酷刑,惩一儆百。然而他拒不低头,坚持要当局把抢走的货物还给他,并且以满腔怒火斥责了镇长雷亚特吉及其帮凶,表现了印第安民族面对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质。他是作者同情、赞赏和着意描写的人物。反动当局对他的非法惩罚,赤裸裸地暴露了官方、军队和奸商勾结在一起残酷剥削和欺压印第安人的丑恶嘴脸。雷亚特吉镇长是反动当局的代表,他是靠压榨印第安人的脂膏发家致富的。他名为镇长,实为强盗和走私犯。他曾同投机商人富西亚合伙倒卖,事发后却平安无事。用富西亚的话说,“这个家伙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比我抢得更多”;他的手下人、后任镇长堂法比奥则认为雷亚特吉和富西亚是“一丘之貉”。这个人物就是作者所说的“张着血口喷射毒焰的恶龙”的化身,是虐杀印第安人的魔鬼,是作品重点鞭笞的对象。富西亚几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狡诈诡秘,心狠手毒,荒淫透顶。他是个日本走私犯,当过海盗,贩卖奴隶,盗窃主人的财产,坑害狼狈为奸的同伙,出卖一同越狱的囚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甚至把老婆也拿去做买卖。他曾闯入印第安人的住区,在一座孤岛上建立了据点,骗取了土著居民的信任,把印第安人的橡胶和毛皮等运往外地,牟取暴利。他还肆意抢劫和奸污印第安少女。最后他患了热病,害了烂疮,被他的老塔档阿基诺送到了麻风病隔离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眼睁睁地等着烂死在与世隔绝的荒地里。这是一个为非作歹、坏事做尽的社会渣滓,是作者愤笔怒斥的社会余孽和危害人类的毒瘤。他的下场正是作者一再指出的腐朽社会的写照:它同样也在一天天烂下去。堂安塞尔莫是《绿房子》的另一个中心人物。他是个外乡人,行动十分神秘,并且身份不清,来历不明。他来到皮乌拉城,举止大方,乐于交际,很快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不久他即在城郊的沙漠地区盖起一幢引人注目的绿色住宅,这就是皮乌拉的第一家妓院——“绿房子”。远近的嫖客纷至沓来,喧闹的噪音,通宵的夜生活,单个儿或成群的人们黎明时分返回城时的放肆的笑声和歌声,顿时打破了这座雅静城池的安宁。他的挑战获得了成功,于是冷眼旁观。站在高楼上观赏人们千奇百怪的丑态。堂安塞尔莫身为妓院老板,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淫荡下流、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他一方面对那个失去双亲、又瞎又哑的不幸孤女安东尼娅怀着诚挚而炽烈的爱,对他的竖琴和音乐,对他的故乡和皮乌拉城曼加切里亚区的穷有着真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也不和那些嫖客、地痞流氓们同流合污。在作者的笔下,这个神秘人物仿佛是拔苗助长地派到伊甸园去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毒蛇,他到皮乌拉来开设妓院正是为了向那种表面与人为善的道德提出挑战的。他的挑战获得了成功,因而激怒了皮乌拉的宗教势力。加西亚神父气急败坏,在城里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抵抗这来自“地狱的威胁”,否则灾难将殃及全城。他带领一群妇女,举着火把冲出城去,一把火焚毁了“绿房子”。堂安塞尔莫从此无家可归,只得靠弹琴为生,组织小乐队在城郊的曼加切里亚区漂泊流浪。他死去的时候,人们称他为“皮乌拉的光荣”,“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者描写这个人物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他的戏剧性的一生,嘲弄和揭露宗教道德的伪善面目,暴露秘鲁社会的腐朽本质和人们的真实灵魂。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其他一些各具特点的人物,例如“绿房子”的第二代主人、带有男性气质的琼加,屡遭不幸、安于命运的残废孤女安东尼娅,修道院里那些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的伪善嬷嬷,终日在迷幻药中寻求解脱的江湖浪人潘塔查,貌似公允、实与反动当局狼狈为奸的律师波蒂略,还有厌恶军旅生活的逃兵涅维斯和那些专门打架斗殴的流氓无赖“不可征服的人”,等等。
《绿房子》的人物,以各自的身份和行为活动在城镇、丛林、河川、孤岛、妓院、酒吧、官邸和修道院,构成了一幅具有丰富社会内容和时代特点的人物画卷。
《绿房子》的语言也有特色。巴尔加斯·略萨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十分擅长驾驭语言,讲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和效果。他勇于创新和尝试,绝不沿用陈旧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个人的独特风格:描写事物或故事时,用语确切,言简意赅,时而含蓄,时而明快,富于表现力;描写人物的对话时,言语通俗,说出的话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反映出人物的特征。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描述人物的对话、独白,标点符号时有时无,甚至将动词也省而不用。这些特点无疑是使《绿房子》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绿房子》历来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高度赞扬。智利批评家路易斯·哈斯热情地写道:“这部作品和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与巴西吉马良斯·罗萨的《广阔的腹地,曲折的小路》一起,是拉美文学中最完美的三四部小说。《绿房子》的结构设想庞大,感情充沛,文笔优美,雄浑有力,每页表现的想象力有如高山瀑布。一个庞大的血液循环系统通过全书的无数毛细血管维持着作品的生命。书中的情节和事件仿佛间歇性的岩浆喷射,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巨流。开卷不久,读者就被催眠迷惑,稍不留意,就会被巨流的旋涡卷去。如果不是篇幅浩繁,真可以不辞手地一气读完,因为尽管语言拖沓,情节安排上却处处有悬念。场景重叠,不同的时空互相交叉——‘连通管’发挥了最大效能,回音先于呼唤,意识活动几乎还未加辨认,便像叹气一样四下散去。每翻一页,都可能迷失方向,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抓住作品的每条线索。”[9]
巴尔加斯·略萨本人谈到《绿房子》时说:“《绿房子》这部小说试图描写秘鲁现实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位于秘鲁最北端的海滨城市皮乌拉,该城是西班牙人来到秘鲁时创建的,城市周围是一大片沙漠,我常常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想起它。皮乌拉的形象具有激发幻想和想象的巨大力量。我虽然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但我的许多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小说运用了我对皮乌拉的经历的回忆。皮乌拉是我的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之一。另一个世界不同,是丛林,是亚马逊,是上马拉尼翁地区的一个小地方,是1958年我从欧洲回来之前几个月短暂认识的一个地区,一个直到那时才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秘鲁的另一张面孔,一个原始的世界,一个秘鲁男人和女人依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世界,它实际上和西方文明、秘鲁文化没有联系,一个也是国家边缘的、冒险家们的世界,那里没有法律,不受城市化的秘鲁的制度的支配,一个充斥着冒险活动、开拓者、考察者、暴力、野蛮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不仅对个人还是对我一直不了解的大自然来说非常自由的世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