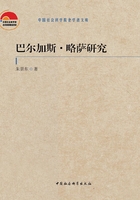
《城市与狗》(1963)
《城市与狗》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先后获西班牙简明丛书奖(1962)和西班牙批评文学奖(1963),最初作品取名《英雄的居所》,后来又改为《说谎者》。此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开启了秘鲁小说的现代时期,同时也和拉美其他作家的作品一起开创了拉丁美洲60年代的文学“爆炸”运动。小说一版再版,迄今已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曾被西班牙《世界报》评为20世纪西部最优秀的西班牙语小说之一。
巴尔加斯·略萨1950年和1951年在利马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受过两年中等教育,这种经历或者像他说的“冒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几年后(大约在1956年),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并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一部小说应该以他在军校的那些经历为基础写成。由于获得去西班牙学习的奖金,无暇顾及,所以直到1958年秋才开始动笔:是年在马德里一家名叫‘小蜗牛’的酒馆开始写,1961年冬在巴黎的一间顶楼完成。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是很辛苦的。1959年初他在写给他的朋友阿伯拉尔多·奥根多的信中坦言:“写小说时,我感到十分辛苦……修改一页要费几个小时,写好一段对话也是这样,突然我又连续不停地写了十来页。对于如何结束,我毫无概念。但是如醉如痴,我觉得写作是真还令人激动的事情。”
智利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哈斯也曾谈到巴尔加斯·略萨一丝不苟、认真写作、追求完美的创作态度:“巴尔加斯·略萨是主张作品要尽善尽美的。作品问世前他总要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作品的各个方面。从第一个灵感的火花开始直到作品出版,他总是不轻易定稿。他经常用放大镜审阅和修改校样,甚至在付印前的最后时刻,他的书桌上还堆满了批注、清样和手稿。为了同出版社讨论要删掉的七八行字,《城市与狗》几乎搁置了一年零六个月之久。”[4]
书稿共1200页,他把稿子寄给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多家出版社,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尽管他的短篇小说集《首领们》(1959)刚刚在西班牙获得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奖,他这第一部长篇还是不能超过弗朗哥独裁当局的检查。他在巴黎时曾请法国的西班牙文化工作者克劳德·库冯看了他的手稿,他很喜欢小说的故事,建议他把书稿交给巴塞罗那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出版人卡洛斯·巴拉尔出版,因只有他能够找到办法巧妙地避开西班牙当局的检查。
卡洛斯·巴拉尔收到书稿后,还未开始看就收到他的顾问寄来的不能出版的报告。尽管如此,有一天巴拉尔感到无聊,便把放在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的书稿找出来翻阅。刚看了第一页,他就被小说的故事惊呆了。他立刻决定千方百计将书出版。不过,他建议巴尔加斯·略萨把书稿投给简明丛书奖评委会。书题为《英雄的居所》(英雄的居所是指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莱翁西奥·普拉多是在1879年的太平洋战争中被智利军方处决的秘鲁军事首领)。不出所料,真的获了奖。评委会成员、西班牙著名批评家何塞·玛丽亚·巴尔维德指出:“此作是《塞贡多·松勃拉》[5]以来最优秀的小说”。
经过漫长的交涉后,小说经过了当局的检查,终于在1963年问世,并随即赢得西班牙批评奖。
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利马莱翁西奥·普拉多军校,学校的青少年(士官生)在严格的军纪下接受中级教育。学校里有一个团体,专门在校内制造恐怖和暴力活动。其无可争议的首领是可怕的“美洲豹”。按照该首领的指令,士官生波菲里奥·卡瓦在考试前一天偷了一份化学试卷,不料被人从破玻璃窗口看见。当局进行查办,最大的受害者是名叫“奴隶”的小伙子(真名叫里卡多·阿拉纳),周末他不能去看他的未婚妻特雷莎。“奴隶”揭发了卡瓦,被开除出学校。“奴隶”请求他的同学阿尔维托代他去看特雷莎,并向她解释他不能去看她的原因,但是她不再给“奴隶”写信,他为此深感痛苦。后来,学校举行实弹演习,“奴隶”的头部被子弹击中,不久死亡。学校当局害怕丑事外扬,便称这是一个意外。阿尔维托(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好孩子、“奴隶”的朋友)不顾和小团体有关联的盟约,向学校比较正直但也颇严厉的甘博亚中尉揭发了“美洲豹”杀死“奴隶”的罪行。但是要求对此事必须保持沉默的盟约也包括学校、老师和武装力量。阿尔维托屈顺于长官们的压力,甘博亚除了屈服也没别的办法。这样,事件没有进行调查而被封锁起来。小说在尾声中讲述学生们毕业,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甘博亚听完“美洲豹”的坦白、但是不能同意,之后他便去山区的哨所服役了;阿尔维托重新开始过米拉弗雷斯他那种资产阶级生活;“美洲豹”被剥夺了原有的一切权力,回归社会当了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并成为特雷莎的丈夫。
总之,小说反映了军校士官生的生活和其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了军校士官生如何深受反动当局的压迫和迫害的情形。士官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学习动机。但在学校当局的严格训练下,都要被培养成合乎军事当局要求的军人。学校当局的压迫、专断、欺骗和摧残,严重损害了那些青少年的心灵。狡诈凶残的上校校长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代表。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子,实际上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要是反抗,他便凶相毕露,残酷镇压。在以他为首的学校当局的控制下,学校变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牢笼,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一座集体大监狱”(作者语)。由于恶人当道,结果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作者以愤怒的笔触对黑暗的学校当局做了无情的嘲笑和抨击。小说像一把尖刀,刺痛了学校和秘鲁军事当局的神经和脓疮。盛怒之下,他们把刚出版的一千册小说在校园里付之一炬,并把作者宣布为学校和秘鲁的敌人,说他是共产党人。
小说无疑是对现今秘鲁社会现实的针砭,是对其社会矛盾的暴露和分析,是个人在那种罪恶的社会中的遭受的不幸的见证。智利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哈斯的评说可谓入木三分:“书名本身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它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狗咬狗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关键部分是暴力,是弱肉强食,只有强者或适应环境者才能生存。作者描绘了一幅灵肉腐烂的悲惨画面。作者的笔锋针针见血,绝不手下留情。这座学校不仅以其环境和地形而且以真实名称出现在小说中。作者对学校的描绘相当逼真,因而引起官方的震怒”,“将一千册书当众销毁”。[6]
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重要人物的形象。一个是“美洲豹”,它是贝亚维斯塔省卡廖县人,其为人强势、机灵、勇敢。这种性格是在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进入军校后,令同学们敬而远之,他打破了学生们的传统:不允许别人给他起外号,他自称“美洲豹”,因为他能灵活地逃避惩罚,并且能机智地惩罚别人。他凭着这个绰号,召集他的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团体,企图以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勇气对付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和不公正对待。在学校生活中,“美洲豹”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千方百计进行自卫。他面对任何形势都不妥协,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他无人可比的优势,不准任何人欺侮他,从而牢牢地掌握着对其他同学的控制权。
在整个小说中,“美洲豹”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以军校为背景的情节中有他,在小说里插入的各种故事中也有他。但是最初,他的身份并不为人所知:他是个少年,以第一人称讲述他在进入军校前的生活,那时他和母亲住在贝亚维斯塔广场附近一个朴素的家中,他在卡廖五月二日学校读书,他还讲述了他对邻居家的同龄女孩特雷莎的爱恋之情。放学后他常去看她。同样他也讲述了在坏同学的影响下成了扒手的情形。后来,他逃出家门,跟他的教父教母一块生活,不久教父教母把他送进军校。小说最后一部分揭示了这个男孩的秘密:他和他童年所爱的女朋友特雷莎结了婚。无疑,“美洲豹”是拉丁美洲社会底层的代表,他有大男子主义思想,他强烈地反对他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他朋友“瘦子”依盖拉斯说他已经变成一个正派的人了。
第二个主要人物是特雷莎,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在作者笔下,她似乎是一个快乐、纯净、娇生惯养的女孩,在三个男孩(“奴隶”、“美洲豹”和“诗人”)眼中,她是一个完美的女神。在小说的一些章节里,三个男孩都对她深怀爱意,崇拜之至。
“所有的男人都有一些共同点,尽管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是人自身的条件造成的。”这是作者想通过特雷莎之口告诉人们的看法。他们都渴望得到没有的东西,渴望被女人爱,需要精神生活。作者强调精神上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比物质和经济的东西更重要。他把特雷莎写成一个有尊严、爱干净的女性,他是想强调,尽管她几乎一无所有,人的本性是不能丧失。
对爱恋特雷莎的三个男孩而言,要想在军校呆下去,就必须离开她:对“奴隶”来说,在熬过严酷的生活之后,他渴望的是平静;对“诗人”来说,被迫上军校就等于失掉了纯朴的天性;而对“美洲豹”来说,真正的家庭生活从来就没有。
小说开始时,作者讲述了“美洲豹”对特雷莎的痴迷,并讲述了为了爱她所做的一切。“美洲豹”小时候总想和她在一起,他找她做功课,上学的路上老跟着她。
后来,“美洲豹”消失了,出现了“奴隶”。“奴隶”天真地追求特雷莎。再后来,通过“奴隶”,“诗人”认识了特雷莎,他和他们一样也常去看她。在他眼中,她是那么完美,那么纯洁。但是在“奴隶”死后,他放弃了对特雷莎的非份之想。最后,特雷莎和“美洲豹”又走在了一起。“美洲豹”离开军校后,又遇见了特雷莎,他提出和她结婚,她欣然答应。
“奴隶”名叫里卡多·阿拉那,他是第三个主要人物。此人性格温顺、听话,这是因为自幼生活在一个女人们决定一切的家庭里。他父亲专断独行,硬把他送进了军校。由于他经常扮演受害者角色,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奴隶”。他在上军校之前就认识特雷莎,他虽然不主动,但是深深暗恋着她。然而,一种不幸的命运降临在他头上:“美洲豹”为了报复,把他打死了。但是这一悲惨事件被学校当局压下了,因为维护这所名校的名誉对当局来说更重要。
显然,“奴隶”是社会容不下的少数人的一个代表,他总竭力想被社会接受,最终却只能成为当局沿用职权的受害者。
“诗人”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是第四个主要人物,他是五年级的学生,由于他善于写黄色小说和情书,用来换钱和香烟,成了学校有名的“诗人”。他面孔白净,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
进军校时,他几乎还是个小男孩,他来自一个已经解体的家庭。跟大多数学生一样,他很不习惯学校强加给他的那种陌生的生活方式。
和军校的其他学生一样,“诗人”必须在校内和校外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在校内他必须表现得麻木、粗鲁、冷若冰霜,不是一个好斗者,总设法避免与人吵架,免得招来是非,总之是明哲保身。而在校外,对他那两个住在同一居民区的朋友蒂科和普卢托,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对他们,他没有必要表现得麻木或不随和,因为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安全,彼此之间不会发生暴力行为。
尽管两人的为人不同,“诗人”还是成了“奴隶”里卡多唯一的朋友。然而他也爱恋着特雷莎,虽然她是里卡多的女朋友。这表明当时他并不看重他跟“诗人”的友谊。
在军校举行的一次实弹演习中,“奴隶”里卡多被打死,“诗人”阿尔贝托认为,“奴隶”之死是有人对“奴隶”进行报复,因为他揭发了山里人卡瓦偷试卷的事情。事件发生后,阿尔贝托觉得必须查出杀死他朋友的凶手,他指控“美洲豹”是凶手。但是当上校讹诈他,并恐吓他说,如果他不撤回他的指控就开除他(理由是他“腐化堕落,精神上有毛病”),他退却了,他想到他的职业,便永远服软了。他回到他的阶层和繁华的米拉弗洛雷斯区。总之,恢复了他那种虚伪的人格。他这个感情脆弱的人,终于走完了他残忍的路程,尽管还残留着几丝正派的气息,但是腐化堕落却安逸地在他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当然也在他未来的生活中扎下了根:他家将有游泳池、敞篷汽车、工程师职称、同一阶层的妻子、一大群情妇、去欧洲旅行。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除了这几个主要人物,还应该提一提那些“狗”。“狗”,是指军校一年级的学生,是高年级的学生给他们起的蔑视性的绰号。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学生们觉得军队就是一个男子气概的训练场,他们必须经历几个阶段,忍受牺牲、凌辱、暴力,获得士官生的资格,即从狗变成人。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第一次熟练地运用他拿手的“连通管”技巧。巴尔加斯·略萨给它下的定义是:“发生在不同时空和现实层面的两个或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述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述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等,从而会与分开叙述的方式大不相同。如果让这种连通管术运转起来,当然只有简单的并列是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叙事文体中被叙述者融合或联结在一起的两个情节要有‘交往’……没有‘交往’就谈不上连通管术,因为如上所述,这种叙述技巧建立的统一体使得如此构成的情节一定比简单的各个部分之合要丰富得多。”比如在《城市与狗》中,作者把关于母鸡的故事同那个鸡奸少年的场面有意穿插起来描写,按照他的说法,这两个故事就像两根连通管。他说,其目的在于有意制造“含糊不清,也就是说,把不同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两个故事或多个故事联结在一个叙述单位里,以便使每个故事中的精华互相传播,互相丰富”。
同样,小说也采用了“中国套盒术”表现手法。所谓“套盒术”就是大盒中套一个小些的盒子,小些的盒子再套一个更小的盒子,这样无限套下去。在小说中,就是一个故事里再讲一个故事,这样讲下去。例如在阿拉纳被杀的故事中双双套入了一些别的故事,如“美洲豹”与特雷莎的恋爱,阿尔贝托的家庭生活等。
小说具有侦探小说的典型特征:这里有违犯学校规定的严重犯罪行为(盗取试卷的劣迹);有当局强加给学生的惩罚(周末不准离校);有对盗窃行为的告发(“奴隶”告发了试卷盗窃者卡瓦);有告密者的死于非命(在演习中“奴隶”被“美洲豹”打死);有无辜者的控告(阿尔贝托不承认杀了人,坚持认为是“美洲豹”为报复而杀了“奴隶”);有事件的不正常处理(学校当局避免丑闻外扬而不追究杀人犯的责任)等。
在结构上,小说由两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包括8 章和一个尾声。每一个大部分前面都有一段题辞,题辞起着引导读者走近小说世界的作用。每一章又分为许多节段,节段与节段之间用空行隔开。每个部分的开头都使用大写字母。只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不分节段,在这一章中讲述了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形,在演习中里卡多·阿拉纳被杀死。第一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各包括10个节段。这样的结构形式,这样的章节划分,使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变得十分清晰,时空的变换毫不突兀,有利于读者一步步进入小说世界。
在写这部小说时,巴尔加斯·略萨曾产生过一些困惑。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写此作时有过许多疑问,不知那个年轻人是不是被一个同学杀死的,还是他的死亡是个意外。反正我的想法不太清楚。所以我把故事写得模棱两可。后来我跟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即罗杰·卡刘斯[7]交谈,顺便说一下,他是评论诗歌和拉美‘爆炸’小说的第一个欧洲人。他谈论《城市与狗》的方式让我非常吃惊。他说:‘美洲豹杀死那个男孩的事件,我觉得是你的小说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回答说:‘不过,如果美洲豹没有杀那个士官生呢?’他说:‘当然他是杀人者,毫无疑问。你没有意识到,但是问题很清楚。美洲豹这个人需要恢复他失去的对同学们的领导权。他是首领,是寻衅打架的人。他要某种方式充当这个首领。那么,他怎样恢复这种领导权呢?那就通过流血事件。只有他可能是杀人犯’。他的话很有说服力,我相信了。现在我坚信美洲豹是杀害‘奴隶’的凶手。”于是他就按照罗杰·卡刘斯的说法描述了“奴隶”被杀害的故事情节。
在论及《城市与狗》创作方法时,巴尔加斯·略萨说:“我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一种我至今仍然忠实遵循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差不多是这样的:写第一稿,即草稿时,我设法将和我喜欢讲述的内容有关的一切可能的想法都写进去。写得很快,以便用这种方式和最初实施这个文学计划时强烈感觉到的犹豫不决做斗争。然后,等我把一切可能的故事成分成功地汇集在这部混乱的手稿中后,便开始重写,这就是说,主要是裁剪、重组这些材料。第二稿,常常还有第三稿,对我来说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因为这让我感到开心,令我振奋,令人鼓舞,激动人心,和写第一稿时不同,那是一种和沮丧、消沉与失败的感觉进行的斗争,只有把这个故事写完才能消除它们。我知道我想讲述的小说就藏在丛林当中,我必须设法把它从这座丛林、第一稿的混乱中抢救出来。直到现在我写所有的书用的都是这个方法。”
他还评价这部作品说:“《城市与狗》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具有些许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描写了一场风波,从而打破了秘鲁小说世界的狭窄界限。当然这场风波十分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军人们读了小说,他们至少知道,小说讲述的是什么,于是他们就在作为小说故事发生地的军校当众把小说烧毁。奇怪的是,他们把小说烧了,但并没有禁止它,结果这一行动成了小说能够得到的最为异乎寻常的宣传,所有的人都想读这本应该烧毁的书。一夜之间,我发现我这本书的读者达到了我从来梦想不到的成千上万个。”[8]
在谈到《城市与狗》时,巴尔加斯·略萨曾这样说:“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写此作时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我找到了一种一定和我个人的人格有关系的写作方式,我采用了一种在后来我的作品中我一直运用的技巧。我相信,任何一位作家在开始写作时都不知道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他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认为头几部作品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