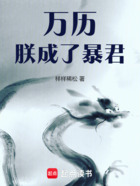
第59章 不旌不表,避雷针
或许是大了两岁的关系,朱翊钧感觉刘姐姐其实挺好的。
不管是亲密的二人运动,还是平常的相处,有种如沐春风的舒惬感。
“对了。”朱翊钧想起一事,开口说道:“朕让太医院派太医,每半月入宫例行诊脉一次。”
刘昭妃看着皇帝,问道:“是后宫妃嫔吗?”
朱翊钧点了点头,说道:“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例行诊脉,也包括朕。”
“万岁想得周全,更是仁心关怀。”刘昭妃露出感激之色。
朱翊钧笑了笑,提醒道:“朕让太医院派年岁大的老大夫,这样就不用避讳。”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别信什么悬丝诊脉,多是故弄玄虚。诊脉时,腕上盖块纱帕也就是了。”
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在明代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
有些贞节烈女,那真是被陌生男人碰了手,都可能断腕以求清白。
朱翊钧看不上这个,也决心逐步加以改变。
各地所报,礼部奏请的要旌表的名单,朱翊钧已经压下不批。
旌表制度在明代远比前代更受重视,并形成了一套严密而规律化的制度。
承袭元代的制度,贞节旌表可分为“节妇”和“烈女”。
节妇定义为三十岁之前丧夫,守节到五十岁以上的妇女;
烈女较无明确定义,但一般是指妇女为维护自身的贞操而死的行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焉。
本来,明代以前,贞节的观念虽然一直存在,且被认为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道德。
但实际上,从未被推广实行于一般人。
即使是宋代理学提出女性守节的主张,也仅是一种对少数士大夫家庭妇女的要求。
所以,在宋代,妇女改嫁还是十分正常的事。
但到了明清,朝廷对于旌表的重视,便形成了一种“守节才是正常”的社会氛围。
这使得妇女在压力之下,即使生计发生困难,还是坚持守节。
乡老、族长、家长等,更逼迫妇女守节,以得到贞节牌坊的设立,并以此为荣。
朱翊钧知道只凭一纸诏书,并不能改变人们已经根深蒂固的陋习和观念。
而且,如果他公开废除旌表,鼓励改嫁,没准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两位太后。
但他也要一步步走下去,并不能因为难而不去作为。
想要变成朱翊钧希望的样子,肯定不可能。
可他看不惯的陈规陋习,又是能力所及,不改就说不过去了。
“臣妾听万岁的。”刘昭妃只是略微犹豫了一下,便乖顺地应承。
朱翊钧笑着点头,给她夹了个小包子,说道:“尝个肉馅的,别老吃素。”
刘昭妃绽出开心笑容,咬了一口肉包子,汁水在嘴中绽开,味道鲜香。
“好吃。”刘昭妃点着头,眼神如水,不时看向变化极大的皇帝。
用过早膳,朱翊钧喝过一盏茶,才起身离去。
早朝的时间改了,朱翊钧还准备对御门听政的地方进行改造。
除了大朝,常朝的地方也改在了建极殿,并对参加的官员又进行了甄选缩减。
阁臣和六部九卿,是常朝必到的。
有本上奏的官员,陛见陛辞的,亦可列席。
朱翊钧还是采取了报备制,第二天常朝的官员数量便能提前掌握。
呼呼拥拥的一大堆人,就是点个卯露个面儿,瞎折腾什么?
有事就来,没事儿边去,看着就心烦。
建极殿空间足够大,百八十人也能容纳。
如果是大朝,就改在皇极殿,也就是后世的太和殿。
如果算上太和殿大广场,容纳几万人也不在话下。
此时,参加常朝的官员们纷纷向建极殿走去。
他们路过皇极殿时,都不禁抬首观瞻。
除了宫殿的高大巍峨庄严外,两根突兀而起的尖刺直冲天际,引人注目。
张四维和申时行对视一眼,都露出疑惑和无奈的神情。
这是皇帝命人加班加点赶制的,三大殿都有。
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也正在加工树立,皇帝称之为避雷针。
“这玩意儿能避雷?!”官员们嘴上不说,心里都犯嘀咕。
但皇帝高兴就好,不过是几根铁柱子,又没劳民伤财,就是有点碍眼。
这紫禁城都是皇帝的,随便折腾去吧!
要说这皇宫殿室,历史上挨雷劈的次数真不少。
就这皇极殿、建极殿,都是烧毁又重建的。
古代人不懂这个,往往归咎于天罚,归咎于德行有失、施政有误。
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不到百日,紫禁城的前朝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被雷击毁于火。
朱棣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因此不敢再在此地办理朝政。
根据历史记载,明清时期,紫禁城大约经历了二十余次雷击。
其中皇极殿多达六次,建极殿多达五次。
按照物理知识,建筑物越高,遭雷击的概率越高。
朱翊钧自然要紧着最高的先来,三大殿自然是排名在前。
一来是防火,保护文物,珍惜生命,也省下重建的钱;
其次,则是防着不懂科学的土包子,借机在朝政上瞎哔哔。
群臣来到建极殿,入内排班肃立。
几声响鞭,内官的尖利声音响起,皇帝升座。
“这龙椅坐着不舒服,光图精美啦,不考虑人体工学。”朱翊钧吐着槽,坐了下来。
皇帝的宝座叫髹金雕龙木椅,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与平常座椅不同,它有一个“圈椅式”的椅背,四根支撑靠手的圆柱上蟠着金光灿灿的龙。
底座不采用椅腿,椅撑,而是一个宽约两米半,进深一米多的“须弥座”。
通体髹上黄金,显得富丽堂皇又气势威严。
“微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张四维率领群臣叩拜山呼。
朱翊钧清朗的声音在殿内回荡,“众卿平身。”
众臣谢恩后,起身恭立。
张四维轻咳一声,上前禀奏。
都是已经票拟批红的奏疏条陈,再走一遍请旨执行的流程。
“……自即日起严禁官窑民烧,若有违犯,严惩不贷。”
朱翊钧轻轻颌首,朗声道:“准奏,下旨颁行。”
明朝制瓷业中有一种“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
但官府出价极低,若烧不成,还要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