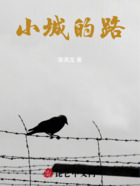
第4章 擂鼓
从楼下的水饺摊回来,杨鹏举已是汗如雨下。线香燃过后残余的烟味有的藏在开裂后翘起的墙皮背后,有的躲在八仙桌和太师椅的下面,有的径直钻进客厅里分隔出来的那两间木板房,如今又都被热气烘了出来。香大爷和边大娘所住的六楼是最高层,屋顶被太阳暴晒了一整天,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屋里积聚的热气还未散去,活像个大蒸笼。杨鹏举住的那一间木板房,没有吊扇,更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爱特”牌小风扇摆放在床头柜上。他从书袋里拿出《李太白全集》,头靠木板,在床头半躺下来。身旁的风扇叶片在高速旋转,它的嗡嗡声怎么也钻不到杨鹏举平静如水的心里去。不知什么时候书里夹进一片枇杷叶,叶上带的潮气已将夹着它的上下几页纸浸得松松软软,起了皱。那片枇杷叶压在《清平调》第二首上,杨鹏举赶紧把它拿开。
客厅的狭窄和闷热,让杨鹏举联想到老家院子的宽阔和穿堂风拂过人身时的惬意。老家南依黄河,北临中条山。整座村庄静静地躺在丘陵的低洼处,山不缺,石不短,树不少,水够用。他自幼在河滩边、沟壑里玩大,听惯了黄河的水声,闻惯了青草和泥土的香味,异域的山有水之地,对他来说不新也不奇。他的老家黄土厚实,但不肥沃,准确地说,是有些硗薄。若是遇上旱年,庄稼会一片片地晒死,枝叶白花花的,跟下了雪一样。能排上队灌溉的田里的产出,不能维持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就只能吃老底了。然而村人大多安土重迁,他们并不稀罕外面的世界,觉得只有自己的双脚踩在松软的黄土上心里才会踏实。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至多骂骂天――他们不会也不敢骂地,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把地骂了,地里就不再长东西了――骂过了,就心平气和了。正如村人所想的那样:这个世界,除了山水,再除过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剩下的就是会两条腿走路的人了,不管走到哪里,不都是一样的么?!村人习惯了山沟里的空旷和宁静,不习惯城里的高楼蔽日和喧嚣。村人喝惯了甘甜的井水,嚼惯了细腻的馒头水饺刀削面。村人乐于栽瓜种豆,亦乐于牛羊满圈。
父亲和大多数村人一样,正直,纯朴,善良,身强力壮,但他不想一辈子用粗壮的胳膊、有力的双手去握铁锹和锄头。他的眼睛似乎比村人转得快,看得远。他的耳朵似乎也比村人长得大,听得多。一九八一年,改革之风越过黄河,吹暖了杨鹏举老家的山沟。那年阴历九月,冬小麦刚刚播下,村子里便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都按人头分到了土地。更可喜的是,村里掌权者的手里,从此手里少了一件拿法人的宝贝――“投机倒把”的大帽子。那时,杨鹏举还未满月,仿佛害怕光亮,紧紧地躲在母亲的怀里,双眼半睁半闭,嗷嗷地张大小嘴找着乳房,找到了,噙在嘴里,怎么也不肯放。母亲后来常拿这调侃:“鹏儿呀,你小时候这么贪吃奶,怎么就没把你给吃胖了呢?看看你这细胳膊细腿,都没人家女子的胳膊腿壮!”杨鹏举说:“妈,那肯定是你当时出奶太少,我总吃不饱,吃到最后,肚子里攒的都是空气,怪不得我现在经常打嗝!”母亲倒认真起来:“刚分地那会,我和你爹麦面吃不上,只能吃玉米桃黍面。油嘛,一年到头就二三斤,炒菜的时候用筷子头蘸上几滴。尤其是桃黍,吃了胃发烧,三天都不㞎;只吃不㞎,上下不通,哪有奶出来?你奶奶倒是育了两只母鸡,人家一天趄着身子成十趟地往鸡窝跑,恨不得把手指头伸进鸡沟子去掏。说起来,鸡蛋确实是个荤星子,可你妈能沾上?蛋刚离鸡沟子,还是热臭热臭的,你奶奶就用袄角撩着,搁到罐子里,嘴里还咕哝:‘蛋就是要热搁,热蛋杀罐里的菌哩!’平常一个都舍不得吃,罐满了,拿到集市上卖,说是要给你姑攒嫁妆钱哩!”杨鹏举问:“妈,那你为啥不育鸡呢?”母亲说:“你爹不是贩猪娃哩吗?平常一些饭菜底子都育猪了,哪有给鸡吃的?再说了,鸡惹虱,我一见鸡心里就不滋润!”
翌年二月二,龙抬头后,村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农具和牛、骡子等牲口廉价转卖给村民。那天一大早,邻居们都涌向巷东头的官房,父亲却躺在被窝里。母亲万般焦躁,在脚地踅来踅去,情急之下,只得掀起被子一角:“人家都去拾便宜了,你咋还睡着不起来?”父亲把眼屎揉掉,说:“都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果不其然!土里的钱,是那么好刨的?”母亲压低声音,怯怯地回了一句:“我头发又不长。”日头一竹竿高的时候,父亲才慢悠悠地起来,去了巷东头。他带回来的是人们挑剩下的三样东西:一把铁锨、一副耧和一把木叉。多年以后,铁锨的把换了,头还没坏;耧一年就用个两三次,所以依然完好如初;木叉不耐用,三个尖齿都磨掉了一大截。父亲说,那把铁锨八毛,那副耧两块,那把木叉五毛。他还说有铁锨,不愁翻地松土;有耧,不怕有墒时种不上;有木叉,不用担心麦碾好了起不了场。
过了三五年,“投机倒把”又不是“投机倒把”了,而且上面还鼓励你干那个。原先集市上的那五六个身穿统一制服、戴红袖章、飞扬跋扈的市管会的人不再到处游走、抓人了,取而代之的是着装不统一,但胸前却别着工商局统一下发的证件的收费员。这些收费员大多由各村推荐,能推荐上的,要么沾了和村里的掌权派同宗族的光,要么暗地里进了贡。然而他们干的是从虎口掏食的差事,遇到脾气暴躁的小摊贩,你要,他不给,一来一去,起了口角,动了手,难免会被打得鼻血染衣,甚至掉了门牙。
其间,公社里时常有工作人员来大队办事,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色高弹呢料衣裳,还骑着亮闪闪的二八式“红旗”牌自行车,像模特一样在巷里穿梭。村人看到后,议论纷纷,说人家城里眼目下就时兴这个。议论完了,便都低头看自己的袄和裤,恨不得和这些工作人员把衣服换了穿。地分了几年,村人的口袋里或多或少都有了货。有了头发,想必没人再愿意去当秃子,让人奚落了。
父亲看在眼里,坐火车去了西安,试着进了一些高弹呢料,还顺便捎带了几十双革皮鞋。这种面料呢,弹性极好,一寸能抻成一尺,一米能拽成一丈;同时光滑无比,虫儿趴着打滑,灰尘黏了下溜。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吃公家饭的,甚至是要饭的,都能穿,关键是穿了显贵气:庄稼汉穿了,只要不看脸和手,就会让人觉得像当官的;当官的穿了,村长看着像镇长,镇长看着像市长;乞丐穿了,保管他看上去像正常人。父亲深信它将倍受方圆十里乡亲们的青睐。父亲把进来的货用架子车驮到公社新开的集市上,货刚一摆开,人们便围过来。你看看,我摸摸,争着将那高弹呢料往自己身上拉,想象着用它做成衣服的模样。第一天赶集,父亲取得了开门红。他的心热起来了,觉得自己找到了新曙光,好比鱼儿游到一块新的水域,那里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其实,父亲更像一条在小溪里游惯了的鱼,不愿意到大江大河里去。他担心那里风大浪大,又有大鱼,随时都会被吞噬。在这条安稳的小路上,父亲踏踏实实地走了近三十年,而且他还要走下去。那俨然已经成为父亲理想的生活方式:虽说个体户地位不高,但是自由自在,不端人饭碗,不看人眉眼高低;卖货的时候,十里八里的乡亲们和你有说有笑,甚至打情骂俏;忙活一天,回到家舒舒服服地睡一觉,睡到自然醒,精神好,胃口棒,吃啥啥香;无公务繁杂之苦,亦无仕途多舛之忧。父亲不知道老子庄子是何许人,更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但却活出了老庄的境界。杨鹏举虽然读了,并且都能理解,但却始终没有父亲那样的洒脱,或许这就是知识使他思想变沉了的宿命。
读高中后,杨鹏举憨憨地跟了一股熬夜的“时尚”之风。当时的校长极力倡导熬夜,入学后的第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用洪亮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是一副唱《渴望》而获得了全县教职工歌唱比赛特等奖的好嗓子――说:“县里的××中学,人家为什么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能有十几个?人家的秘诀是什么?是‘熬――夜――’。你们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人家还坐在教室里呢!”杨鹏举的班主任深入挖掘校长的“旨意”,说:“当兵的死在战场上是天经地义的,无上光荣的,你们作学生的死在教室里,倒在蜡烛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是死了,不也是给自己立了牌坊了吗?你就是不想熬,也得想想你有后路吗?你是人家城里的,爹妈退休了能去顶班?”原本不熬夜、甚至有些鄙夷熬夜者的杨鹏举,也熬了起来。为了保持大脑清晰,杨鹏举还让父亲专门买了健脑提神口服液,每到凌晨十二点,喝那么一支黄褐色的像尿一样的东西。喝了,一阵清醒过后,脑袋还是黏糊糊的。眼睛累了,脑袋满了,放下手中的笔,趴在桌上,双手托腮,盯着蜡烛发呆。暗黄色的小火苗在鼻息的带动下,微微晃动。北大的红楼、清华的白门,在蜡烛的火苗里若隐若现,仿佛在向他招手:“熬吧,继续熬吧,熬过了这一夜,明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离人间天堂更近一步了。”
杨鹏举不仅在学校里熬,回到家里还熬。第二间厦屋里靠着窗台放着一台缝纫机,高度和学校的课桌差不多,杨鹏举拿它当了课桌,还把厦屋想像成教室。父亲看了疼在心里,多次劝说:“鹏娃子,学的东西考试够用就行了。这么拼,真把身体伤了,就得不偿失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看,爹没上过大学,不照样活得潇洒,日子也不弱他人吗?”父亲其实并不希望杨鹏举再走他的生意路,他觉得书读好了,才能高人一头,才能为杨氏门庭添光加彩。父亲爱拿西安城墙下的护城河打比方,说:“鹏娃子,你看看,一道护城河,分出了里外,隔出了城乡。这些都是生就的,爹没法给你。你想要进城,过上城里人的逍遥日子,非得跨河过桥不成。你考大学,就是自己给自己造过河桥。”
有一次,父亲在巷里看人打牌,有好事者嘲讽道:“泰蛋儿,你摆摊子卖货,经风受雨的不容易。挣下钱了买猪头肉吃吃,给屋里添几件像样的家具,要么去大城市游游,到舞厅里跳跳迪斯科,说不定还能交上桃花运呢!快活日子你不想,为啥偏想着把钱撂到书纸上去供你鹏?等你鹏一过二十,索性给他盖几间房,找个媳妇,交代了算球了!”父亲鼻子一哼:“家兴败,看后代。我宁可把钱花在笔头,也不花在墙头。过十年、二十年咱的再看!”父亲压根看不惯邻居们圆溜溜的脑壳里装着的那些浆糊般的想法。父亲虽说做布料生意,但东西是卖给周围乡亲的,收入有多少,那是浊水里放明矾,看得见底的。尽管如此,父亲却总是奉行一条铁则――有限的收入优先安排子女的学费。
客厅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响了八下,钟声古朴,浑厚,像一个陌生人从遥远的过去风尘仆仆地赶来。钟声一过,嘁嘁喳喳的嘀嗒声又清晰了,里面还夹着蚊子尖细而有力的嗡嗡声。楼层这么高,能飞上来的蚊子,肯定非块儿大力壮者莫属。若被它们叮咬,小则大片红肿,起坟头似的大包;大则溃烂流脓,非得剜肉补疮不可。十来分钟后,响起了敲门声。杨鹏举的心像猴子一样跳到香大姐的身上,可是这带着些许嫩稚的嗓音又把他的心推开了。
“奶奶,奶奶,开下门。”一个女孩急切的喊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荡,声音里满是怯意。
“馨怡回来啦!”边大娘从容自若地开了门,仿佛在告诉孙女: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真有歹人尾随,奶奶会用拐棍替你赶走他,“哎,怎么没和你妈妈一道呢?”
“下了晚自习我去火车站喊她了。妈妈说让我先回,她再待会儿,看还有没有要住宿的。”脱掉运动鞋换上拖鞋的馨怡,身形偏瘦,方脸,皮肤略黑,明亮的黑眸子忽闪着――这体貌和香大姐相去甚远,似乎是遗传她父亲的。
“小杨,喝碗绿豆汤吧,解解暑。”馨怡吃饭的时候,香大娘右手端碗站在杨鹏举的房间的门口,“这老天爷真是的,发起威来简直要人命!”
“不用了,边大娘。”
“小杨,别见外。”边大娘把碗搁在桌子上,“快喝吧,不够锅里还有。”。
绿豆汤不稠,但火候已到,绿豆全都煮得开了花,悠悠地软软地浮着,像天上的云在碗里投下的影子。杨鹏举咕咚咕咚喝下,顿时觉得思维清晰了许多,便回头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小风扇。风扇的叶片快速旋转着,恐怕因为塑料叶片疲劳的缘故,吹出的风已经没有了凉意,只剩下一股热风。杨鹏举将风扇的后脸儿对准自己,散开的微弱的凉风才从风扇后罩的缝隙里钻出来。杨鹏举静静地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十指交叉垫在头下当枕头,瞅着低矮而发黑的天花板。困意悄然袭来,然而陌生的床,陌生的凉席,陌生的墙壁,陌生的女人挂历,盯着看了一阵但依然没有产生亲近感的天花板,樟脑球淡淡的臭味,衣物和被子因受潮而散发出的让人皮肤发痒的青苔味,这一切都让他辗转难眠。杨鹏举双眼半睁半闭,朦胧中看到天花板上奇形怪状的图案慢慢突起,一会儿像门楼,一会儿像䦆头,一会儿像花碗,一会儿像人脸,一会儿像父亲开三轮车时戴的头盔,一会儿又像母亲切菜用的菜刀,不过这些图案转瞬又消失了,木板墙还是那个木板墙,天花板还是那个天花板。蚊虫尖细的鸣叫忽然变成坦克的轰隆,接着四面响起了呐喊和厮杀声。良久,周遭才恢复了死寂般的阒静。猛地,两个左嗓子男人嘶哑的对歌声夹杂着浪花拍岸声、汩汩的水流声破窗而入。撕心裂肺般的歌声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只是随口唱出的片段。其中一男扯开粗大的嗓门,仿佛要把楼下的老榆树上的叶子都震落。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另一男故意拉细,拉长了声音:
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
让你亲个够
噢……噢……
“噢……”声冲出KTV包厢的隔音墙,穿过幢幢高楼,飘向空旷、阒无一人的原野。香大爷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起身将门砰上。杨鹏举盯着天花板,眼前出现了一幅幻景:一对恋人在夕阳的橘红色的光亮里,坐在河畔,相互依偎,喃喃低语,时而含情脉脉地对视,时而又爽朗地笑出声来。这幅幻景像一股细流,滋润着杨鹏举干坼的心。
客厅里的挂钟敲到第十下的时候,香大姐在门外喊了声“妈”。边大娘耳朵不笨,一骨碌起了身,开了门。
“妈,来了位高人!”香大姐脚还没跨过门槛,声音却已进了屋。
“哎呀,是位师傅啊!快进来!快进来!”边大娘好像看到神仙下凡,异常兴奋,在原地打转搓手,不知如何是好,“师傅,该怎么称呼您?”
“贫尼法名净慧,阿弥陀佛。”
“净慧法师大驾光临寒舍,让寒舍吉星高照,喜添福寿哇!”
“施主您过奖了,贫尼只是普通的出家人而已。今晚借住一宿,有劳施主了,阿弥陀佛。敢问施主尊姓大名?”净慧法师平缓的声音里似乎蕴藏着淡淡的忧伤。
“免贵姓边。”边大娘诚惶诚恐,“净慧法师,这么晚了,您您是有公务在身吧?”
“贫尼前日去苏州参加佛学会议,乘火车回来晚了。庵里想必已经歇息了,故劳烦边施主一晚。”净慧法师的普通话里透着陕西腔,好比山西的火烧里夹了陕西的猪头肉。
“净慧法师,您别见外。平日里我们供观音菩萨,今天您就是活菩萨。”
“边施主,您言过了。只要您心中有佛,一心向善,菩萨自然会保佑您平安无事的,阿弥陀佛。”
“净慧法师,就说我这个肺――”
“妈,时候不早了,让净慧法师洗漱洗漱,早点休息吧。”香大姐插了话,略显疲惫的声音中露出了些许不耐烦。
“净慧法师,那您先歇着。”边大娘似乎找到了救星,不情愿地转了身。
窗外高远的夜空,繁星点点,不时有拖着长尾巴的流星一闪而过,像在水池中漫无目标游动的小蝌蚪。周围的星星好像受到了惊吓,曳着微弱的银光抖动着,瞬间挤到了一起。潮湿而黏稠的夜色从窗门的缝隙流进千家万户,于是黄色的灯,白色的灯,红色的灯,还有一些挂在阳台上的彩色的灯,都相继熄灭,只剩下无助的路灯,一闪一闪的,和天上的星星说着话。不一会儿,香大爷和边大娘此起彼伏的鼾声便满屋回荡了。远处偶尔几声犬吠也是那么的清晰可辨。
不知怎的,杨鹏举的心脏像鼓槌一样,不安分地在胸腔擂起,仿佛连这个寂静下来了的夜也要擂破。